宗毓华那次采访中有关购买楼房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特朗普人生观的一个有深度的角落,在当时就引起过关注。在其他采访中,通过一些一再重复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到他更完整的人生观。本文就以这些采访为基本素材对特朗普的人格和行事方式做一个大致勾画
老高按:《波士顿书评》网站在2024年大选进入最后冲刺之际,组织了一组文章,分别出自郝志东、倪世杰、程映虹、朱与非、严家祺之手,编为一个专题:《唇枪舌剑:2024美国大选你如何看?》。编者说:“特别选取几种有代表意义的观点,呈现给读者思考与讨论:美国到底怎么了?美国该何去何从?”
大选早已尘埃落定,胜负分明,但是如何看待二进白宫的川普和川普现象,争论方兴未艾,这些文章多数并没有让读者感到过时。
这里我选录德拉瓦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的文章《特朗普素描:与人斗其乐无穷》。中文世界一般人包括我,了解川普,多是从2015年开始,因为他那时决心逐鹿中原。在那之前,我看过他一些电视节目,对他那句“You are fired”记忆尤深,但除了知道他是一位虽未发财、却总能绝处逢生的地产商,了解甚少。而程映虹这篇文章,将我对川普性格形成、思想演变过程的了解,往前推溯了三四十年,实在读来很有兴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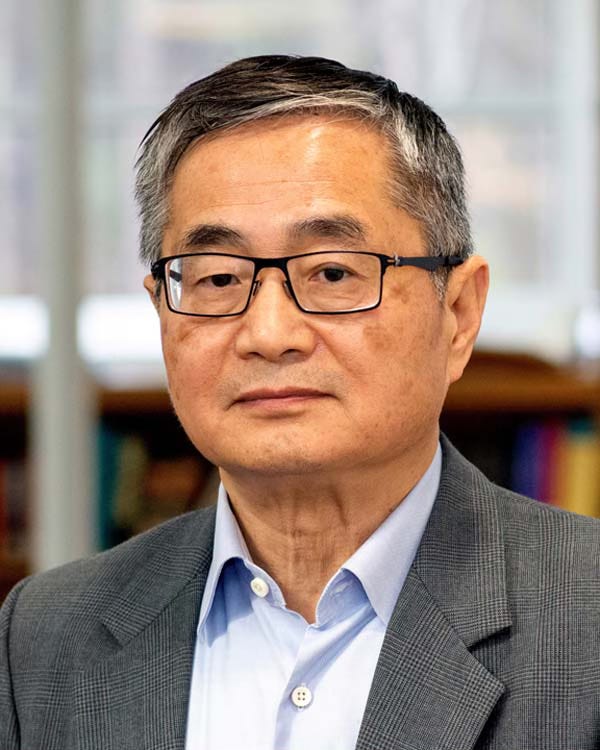
程映虹教授我此前专门介绍过,中英文著作等身,网上可以检索到他大量文章,此处不赘。这篇文章他何时写就,《波士顿书评》网站并未注明。我读来感觉不是近年的,可能是2016年即川普首次竞选之际写的。谈的都是已经发生过的、进入历史范畴的内容,可以供我们更全面客观、更具纵深感地了解川普,更有把握地从他的过去推测他的未来。
《波士顿书评》这个专题的链接如下,有对其他学者的文章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移步前往。
https://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p/2024-4af
特朗普素描:与人斗其乐无穷
程映虹,波士顿书评 Boston Review of Books Oct 27, 2024
1990年的某一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裔主持人宗毓华在特朗普位于纽约闹市区的写字楼采访他。当话题转到“你对生活有何不满足”时,宗毓华的画外音是“特朗普不会有满足感,除非看到下一笔交易”。此时,特朗普和宗毓华走到落地窗前,特朗普指着不远处一座美轮美奂的巨大楼房说自己已经把它买下了。宗问他:“你为什么要买它?”特朗普说:“一想到它在别人手里我就禁不住要发狂。”宗连连追问:“为什么?”特朗普说:“你想一想,我每天都要看见它。它在别人手里,这个感觉太糟糕。这难道不是太糟糕的感觉吗?你每天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窗外最漂亮的楼房是别人拥有的,我感到对不起自己。所以我要买它。”宗故意问:“我也整天看着它,我怎么没有这个感觉呢?”特朗普说:“我们的心态不同。”宗又说:那么假如外面是旧金山湾的跨海大桥,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特朗普说那当然不会。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三十出头的纽约地产商特朗普就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对象。自那时起他接受过难以计数的访谈。宗毓华的那次,是他最不满意的。他后来在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另外一个女记者的访谈中把宗毓华说成是轻浮浅薄的小女孩,问的都是愚蠢的问题,那次采访简直是“disaster”(灾难),他不明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什么花钱雇她。他说自己原来一直认为媒体是值得信任的,但后来改变了看法,举的事例就是宗毓华的那次采访。
把宗毓华那次采访和特朗普经历的很多采访相比,宗的挑战性非常明显,别人暗示的意思她却直白地点出来。例如她说公共舆论都认为特朗普没有对社会做足够的人道慈善回馈,特朗普说自己做了。宗要他举例,特朗普举了个建造老年福利公寓的事例,宗说那是很久以前了。接下来宗问他的人生观,怎样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和某一个人的交往特别让他高兴这样的经历等等。当时特朗普已经很不愉快了,他说有很多人不信任自己,可能也包括你。文章开头那一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从特朗普谈论自己购买那栋大楼的语气神态来看,很有可能是他故意对宗毓华的一种炫耀和反讽。但这恰恰让宗毓华取得了采访的最佳效果,让观众看到特朗普的真情流露。特朗普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塞西尔·罗德斯,英国南非殖民地的开拓者和南非金矿的拥有者,十九世纪末世界级的富豪。他有一次夸张地说:每当看到夜晚头顶上闪烁的星星时,我不可能到那里去将它们征服的想法就会让我发狂。
像特朗普这一类地产商,又经营大量高尔夫球场再加赌场,和靠制造业和高科技创新致富的企业家相比,在美国企业家精神的光谱中位于末端,公共舆论难免视为迹近投机冒险和法外经营,其负面形象几乎是被注定的。一些采访中他甚至被用质疑的口吻追问有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和宗教信仰,有没有想过灵魂的归宿。媒体对这样富可敌国的成功人士不应该再从正面施予公共资源,而是多给批评性的关注,这是社会舆论环境健康的表现,至少在那个时候不是什么“左媒”的抹黑。特朗普本能地觉得媒体都来者不善,但又要依靠舆情的聚光灯扩大影响,打造公共形象。他和美国主流媒体的关系就是这样相互的爱恨交集,但其个性和观点很大程度上还是通过全国性的电视节目得到了传播。
宗毓华那次采访中有关购买楼房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特朗普人生观的一个有深度的角落,在当时就引起过关注。在其他采访中,通过一些一再重复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到他更完整的人生观。本文就以这些采访为基本素材对特朗普的人格和行事方式做一个大致的勾画。
1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斗争
在很多次采访中,特朗普都会面临“对你这样的人来说,生活中什么最重要?”这样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都大同小异。1992年,美国公共广播电台(PBS)的著名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在一个非常正式的六十分钟人物采访中最后问了这个问题。当时特朗普正经历过一次事业和生活的逆境。特朗普说:“我想最重要的是我经受考验生存下来的那种方式,那种让我在激烈淘汰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的方式。”他说很多人在那样的考验和环境下都败阵了,“很多厉害的、聪明的家伙都放弃了。他们就是放弃了。所以我想,我能生存下来,这本身就对我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当他被告上法庭、卷入纠纷、深陷丑闻甚至面临局部破产时,特朗普说,“别人都觉得我这次肯定不行了,但我就是挺了下来。”
尽管在他人眼里特朗普已经是生存斗争中令人羡慕的赢家,但他本人始终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斗争意识,他在采访中说常常有一觉醒来经济崩溃世界末日来临的焦虑。通常商业世界中的“竞争”一词用在他身上并不确切。他的世界观可以说是生命不息斗争不已,斗争让他感到满足。与强大的竞争对手斗,与各地政府的规章制度和行政官僚斗,与各种对抗商业利益的社会团体斗,与形形色色妨碍他地产扩张的大小业主斗,与曾经的伙伴和下属、后来的背叛者斗,斗争的战场从谈判桌到赌场和法庭(据《今日美国报》报道,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特朗普作为被告和原告一共卷入了4000多起诉讼案),而最重要的是与始终变幻莫测的市场斗。斗争成了他的常态和生存方式。虽然历经艰辛和艰险,但多数斗争中他最终都幸存了下来。这个过程不但令他感到其乐无穷,而且滋生和助长了那种“不信邪”的信念。
他眼里只有两种人:不是winner(赢家)就是loser(输家)。生意场上的胜负不但标志事业的成败,而且也被赋予了价值意义。“Loser” 成了他不但对于任何对手,甚至也包括与他完全无关只是被他看不起的人和事的蔑称和夸张用语,从商业到政治和私人生活。他胜选前有媒体就他在公开场合使用loser指称他人做过粗略的统计,约有170多人次。这些人中有商业对手、政界大佬、媒体人士和文艺体育明星,还有他曾经的竞选顾问。无论是谁,只要他不喜欢或是不满意,开口就是loser,甚至是total loser(彻底的输家)。这些“loser”干的事都是“disaster”,或者是“total disaster”(彻底的灾难),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与自己竞争失败的一系列商业对手、阻挠自己项目的政府官员、自己曾经资助过后来对之失望的球队到今天奥巴马的医改计划。
2 美国三十年前就是国际贸易的输家
“输家”和“赢家”也是他评价美国与世界之关系的概念。1987年他在纽约一家报纸上刊登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批评美国政府扶植盟国的经济政策使得日本、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国家的普通人都成为富翁,这些国家“totally take advantage of America”(完全就在占美国的便宜),而很多美国人却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美国领导人使自己国家成为被它的盟国暗地嘲笑的对象。
1988年11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邀请特朗普作为节目嘉宾。当时正值美国经济滑坡和老布什当选总统。莱特曼问,照他看来美国经济会不会崩盘?他说完全可能,美国经济充满危险的变数,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过得不错,他们过得不错完全是因为他们占美国的便宜。美国成了这场贸易游戏中的loser。他说日本就是如此,日本人在美国倾销汽车和家用电器,但却对美国商品和投资设置种种障碍,所谓自由贸易完全是单方面的。中东很多国家也是如此,他们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技术和投资,却高价向美国出口石油。他说美国每年因为这种不公平的贸易损失两千亿美元,这两千亿美元如果用在本国可以干很多事。
有关特朗普的一个错觉是认为他指出了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困境,以此赢得了大众支持。实际上他从80年代就这么说了:我们的政治家很多是傻瓜,是loser,他们让全世界都来讨美国的便宜,自由贸易是单方面的,美国的盟国一面充分利用我们的善意一面暗暗笑话我们的愚蠢和颟顸,就在世界上其他人的生活越过越好时美国普通老百姓却每况愈下,简直是terrible(极其糟糕),美国每年起码损失两千亿美元(这个数字不知他是从那里得出来的,多年未变过)等等等等。
3 从昔日回避苏联到今日的亲俄
看他在80年代的采访中谈到国际形势时,人们根本感觉不到那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对盟国的经济关系必须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评价,美国的亏和赚也不是光用美元能衡量的。实际上,明了冷战过程的人恐怕都会同意,离开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经济上的巨大付出,苏联集团的瓦解是绝不可能的,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更是如此。特朗普说:我不提美国的敌人,敌人是敌人,你和敌人很难谈判,我说的是我们的盟友,是他们在讨我们的便宜。“我不提美国的敌人,敌人是敌人”——就这一句话,他轻轻巧巧就把自己从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中解脱出来,进入他自己创造的国际政治现实,使用他自己的政治术语。在这个政治现实中只有贸易不平衡,在这样的政治术语中只有如何让盟国一起付账。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冷战时期,特朗普从来没有(至少在那些重要的媒体亮相中)在谈及有关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提到过苏联,就像他现在不把俄国视为西方世界的威胁一样。在他看来支配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就应该是真正的自由贸易,美国应该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充分利用这个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成问题的不是苏联,而恰恰是美国的盟友。被最保守的里根总统视为邪恶帝国、与美国势不两立的苏联,完全在他的视野之外。他一方面说和敌人很难谈判,但另一方面,1985年他在纽约刊登的一幅政治广告中又说他相信以自己在商界百战百胜的谈判技巧,他可以和苏联就裁减核武器达成协议。
人们尽可以把这些自相矛盾的话视为吸引眼球的离谱言论,但回想起来,他今天的亲俄姿态,包括俄国情报部门在大选中助他的一臂之力,似乎其来有自,早有不祥的历史预兆。
4 参选总统决不能输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三、四十年前,狼还不知在什么地方的时候,特朗普就对美国人高喊“狼来了”。现在狼终于来了。这并不能说明特朗普是先知先觉,而不过是在他自己的世界观下对社会现实一以贯之的成见。前面说过,他不是靠制造业和高科技起家的,作为一个地产投机商人,他的本行就意味着始终要面对巨大的风险和莫测的未来,他对美国社会四十年来一直存在的危机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自己特定的事业选择和人生道路带来的心理压力,人们却误以为那完全表达了他一直以来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
特朗普最终走上从政之路,是这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结果。他经常悲观地预言美国经济,批评当政者把美国变成loser。所以,很多采访者都问他将来是否会参加总统竞选。1988年莱特曼的采访中,他说美国经济很可能崩盘,莱特曼问那么你本人有没有可能在这场经济灾难中生存下来?他说相信自己有这个可能。莱特曼又问你将来会竞选总统吗?特朗普先是否定,后来在莱特曼的催问下做了很含蓄又很符合他个性的答复:“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看到美国变成赢家——你愿意看到美国变成赢家吗?”
同年在著名的奥芙拉脱口秀中,他回应主持人奥芙拉的提问。奥芙拉说你不久前在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批评美国对外政策,那么照你看应该怎么做?特朗普说必须让盟国分担费用,美国已经负债累累,不能再承受每年两千亿美元的外贸赤字,同时让日本在美国倾销,让科威特普通人都生活得像国王。奥芙拉再问他将来是否会参与竞选,他说自己基本不想,但如果美国的状况确实糟到让他看不下去的地步,他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当奥芙拉再次追问这个可能性时,他说“我还不知道。但告诉你,要是我参选,我可不会作输的打算。我生活从来不是为了输。如果有那么一天,我想我一定会赢的。我不能担保其他的,但我可以担保让那些已经占了我们二十五年便宜的国家付我们大笔钞票。”他提到“二十五年”,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从六十年代初就走上了“邪路”,而当时正是美苏冷战因为古巴导弹危机而激化,美国亟需盟国的时候。
5 人生就是争输赢,无关理念
人生就是非赢即输的斗争,一场零和游戏,从商场到政界都是如此,这就是特朗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冷战到全球化的四十年中,特朗普对公共问题的讨论极少甚至从未涉及价值观、道德观和抽象理念,基本就是以成败胜负论人生和国家。在他看来机会和谈判永远重于原则和立场,衡量得失的唯一标准是以美元计算的收益和亏损,世界和美国的关系就是前者从后者手里骗去了几千亿美元。他头脑中基本没有国际关系和国家利益的复杂概念,更没有美国作为大国的担当。
他对他人的看法也与此相关:不和自己在一起的以赢家和输家来评价,和自己在一起的以是否对自己忠诚以保证自己是赢家来衡量。1992年在查理·罗斯的那次采访中,他深思着说自己有时很想做个loser,以此来测量究竟谁真正对自己赤胆忠心。在他胜选前后的公开场合中,他对别人的介绍和评价基本都是围绕着和自己关系的远近,与其说是在赞扬别人,不如说是把所有这些人放在以自己为基点的坐标轴上。某人“great”,是因为他/她帮了自己大忙。
当选总统后,在参加美国黑人历史月的纪念会上,特朗普不但连官样文章都不愿意做,回避在这个特定场合下应该出现的“自由”、“平等”、“废奴”、“反种族歧视”这些关键词,把废奴斗争中的黑人英雄含含糊糊地说成是“取得伟大成就的个人”听上去像是人生斗争的赢家,而且花了很多时间介绍来宾,赞赏他们对自己胜选的贡献,几乎把黑人历史纪念会变成自己胜选的庆祝会。
6 反精英亲平民姿态的背后
有关特朗普的神话之一是他反建制和精英,和平民大众倒是很亲近。从现象上看确实如此。1988年他作为纽约的商界名人接受正在参选的布什家族的邀请,前往布什家族在缅因州的老家庄园参加名人聚会。记者采访时问他和美国政经界精英的关系如何,他说基本没什么关系,他们不喜欢我,因为他们把我看成竞争对手。他接着说,我倒是和纽约的出租汽车司机很亲近,我和他们话很多。
当特朗普说这话的时候,美国政界可以说根本没人视他为对手,甚至到了2015年他成为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时还有很多大佬视他为笑料。因此,与其说是别人出于竞争心理而忌讳他,不如说是他基于竞争就是生活本质的眼光来看待与精英的关系,而下层民众或者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不是自己的竞争对手,所以相处就轻松自然得多。这种人际关系现象,在二十世纪的独裁者中屡见不鲜:他们对自己的同侪不但保持距离而且严加防备,对下层民众和那些完全不可能威胁自己的知名人士反倒亲切有加。越过精英和建制直接和下层民众交流是这些人为自己打造的公共形象,以此动员下层民众更是他们重要的政治资源。
7 最早的拆房——有钱人的任性
1980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对他的采访是现在可以看到的特朗普最早的一次媒体亮相,当时他只有33岁,但已经在纽约房地产界声誉鹊起,那年他买下了纽约市中心一大块地皮并在上面拆旧建新,但却引起了社会争议。在那块地段上有些历史悠久的老房子,外面有一些十几英尺高的塑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提出应该保留它们,但特朗普将它们全部推倒。
面对记者的提问,特朗普是这样解释他的决定的:我们买下了那块地皮,我们有项目要建,我们确实必须拆毁那些建筑,有很多人抗议和反对,要保留这些建筑,但这些建筑其实没太大艺术价值,我们就把它们都拆了。拆了以后反对的声音就不那么响了,现在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记者又问:拆了房子,那外面的塑像为什么也不保留呢?特朗普说那些塑像很危险,朝房屋一面倒还不要紧,万一朝人行道一面倒会伤人的。
换一个地产商在这样的场合或许会把这段话倒过来说:我们做了很多研究,找了专家做了评估,这些房子并不真的那么有价值,权衡下来还是拆掉了,我们还是很尊重那些要保留它们的人的意见的。而特朗普上来就说那块地皮已经是我的了,我已经做了决定了,这些房子必须拆掉,然后再来说房子其实没有多大价值。看似不同的说话方式和顺序,表达的却是对社会舆论的不同态度和对那些老建筑究竟有无价值的关心。至于拆毁塑像的理由,听上去就勉强,因为如果真要维护塑像,办法多得很。
这个问答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特朗普专断的个性、对文化价值的轻视和藐视舆论的行事方式。用今天中国流行的话来说,是典型的有钱人的任性。特朗普就任后短短一两周,联邦政府已经拟议要大大削减对人文社科和艺术的资助,这完全符合特朗普的个性和喜好。
8 “斗”是特朗普主义最可预测的因素
特朗普现象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特朗普主义”的热议,人们都在预测他的“新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实现他选举中的诺言或者大话,地位和身份的改变又会对他产生多大的制约,或者恰好相反,这种改变会更助长他的自信从而让他在行使权力时更任性。
至今为止,特朗普主义还是美国主流政治中的异端,是一个表面上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例如根据他的言论和获得的相当一部分大众支持,可以说他是 populist(民粹主义的),但根据他本人的背景和内阁成员的任命,也可以说他是 plutocratic (财阀主义的)甚至是 crony capitalistic(裙带资本主义的)。
如果说基于各种因素的制约,特朗普很多国内外政策还有待于观察的话,特朗普现象或者特朗普主义中的一个核心成分是恒定的,可以预测的,这就是被他的世界观和个性所决定的行事方式。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斗”字。虽然国家领导人的世界观和个性都会多多少少反映在他们的施政中,但大概无人能否认,在这一方面,特朗普是最突出和让人担心的。
甚至可以这么说,特朗普的个人意志和行事方式与美国制度、惯例和主流文化之间的不和甚至冲突,以及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传统盟国的关系的莫测,将是特朗普政府最可预期的前景,与此相比他的具体政策走向都是次要的。
认识特朗普主义的第一个层面是用他通俗语言表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视生存斗争为第一要务、以输赢论人生和政治的世界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在他获得普利策奖的名作《美国生活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Life)中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在英国产生,流行于欧洲,但却受到了宗教性更强的美国社会的欢迎(虽然按理说宗教性更强的社会应该会排斥达尔文主义),在美国有更多的信徒。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传播时,正值内战后美国的社会思潮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改革思想和平等主义(集中表现在反奴隶制)后向保守主义的回归,这一点和当今的美国有些类似。霍夫斯塔德说,当时美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基于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和淘汰的逻辑对任何感性的理念的传统的事物的公然拒绝。看来特朗普对任何正面价值的回避,就继承了这一点。
霍夫斯塔德的分析对我们认识美国社会的两面性很有参考价值。美国社会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普世宗教情怀举世无出其右,在它们影响下的美国国策和普通的美国人的行动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但美国同样是个人主义的天堂,推崇个人成功,重视个人利益。此外,美国奴隶制度发展和延续的程度以及后来的种族隔离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必须正视美国社会的这些矛盾,把这些矛盾视为人类本身的局限性,既不把这个国家阴谋化、妖魔化,也不要把它理想化、神圣化。
认识特朗普现象的第二个层面是他的个性和他的世界观之间的密切关联。他一方面视自己为生存斗争的幸存者和成功者,随着商业的成功其个性越来越自负,使得他最终决定参与竞选总统、成为人生最大赢家。但另一方面,生存斗争的世界观又使他一直在强烈的不安全感下生活,始终不能摆脱危机感。极端的自负和极端的不安全感,使得他的竞选语言带有一种浓厚的宿命和天启的色彩,自己成了弥赛亚——“我是唯一能拯救美国的人”(I am the only one who can fix the problem)——这是他竞选过程中包打天下、允诺把整个美国和那些未得利益者或者丧失利益者从loser 变成winner的一句话。他的所谓“大嘴”不是一种夸张的语言风格,而是实实在在地表现了他是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建立在极度的自恋、自大和自负之上的唯我独尊的人格,不能再从商业成功中获得满足;对财富的追求,对声望的追求,最后导向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这样一种动力下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它难以接受既定的政治文化甚至制度规范的约束,导致对舆论、制度和传统的藐视。它超出了一般政治家都具有的鲜明个性和人生追求的范围,甚至超出了所谓“政治强人”的概念,是一种在商业社会中产生的现代社会极权型领袖人格,很接近二十世纪一些被美国主流政治视为专制独裁者的外国政治家。
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挑战建制和精英”,在特朗普现象中更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它是从外部对民主制度的侵蚀,而不是民主制度内部的制衡和调节。即使它不能达到颠覆这个制度的程度,但起码可能造成对这个制度严重破坏性的后果。特朗普就任一个月,行政当局匆忙出台的强硬的反移民政策就遭到联邦巡回法庭的否决。而特朗普毫无妥协和迂回地采取了对着干的姿态,不但像他以往那样对诉讼对手扬言“法庭上见”,而且称联邦法官为“所谓的法官”,其言行不但完全不像一个理解和尊重美国制度、以国家大局为重的领导人,甚至缺乏基本的修养和教养,似乎还生活在那个可以无视公共形象的地产商人的世界中。
这样一个“斗”字当头的人一入主白宫,就把输家和赢家的心态和作风带入美国制度内部的复杂运作,引起了一场其后果有可能产生宪政危机的政治分裂,这无论对美国和世界都绝非福音。
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教训之一就是手中握有大权的统治者的专横和一意孤行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影响。这个历史会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重演吗?一方面,美国的制度设计固然防止了这种现象的出现,美国根深蒂固的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公民社会也仍然健康有力;但另一方面,美国社会的危机和分化是显而易见的,民主制度下党派政治的畸形发展和斗争的激化也已经危及这个制度本身;尤其重要的是大量普通选民对二十世纪在其他一些国家出现的那种政治现象基本没有免疫力,作为选民,他们在社会危机下能否做出超越个人利害关系的理性的选择,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未知数。
重温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两句话此刻非常有意义。第一句是“真相比虚构更离奇。”对很多人来说特朗普的当选就是如此,看似不可能的结果就是发生了。对此我们要有更多的心理准备,美国的制度可能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像保险箱那么牢固。第二句是:“历史不会重演,但其主旋律会周期性出现。”这里的历史,指的就是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可能正在经历世界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
近期文章:
一位享誉世界的政治哲学家如何看待左派的筋疲力尽
关于“民主,何以为继”的一点困惑
川普摸准了“后真相时代”的脉搏。咱们摸准了吗?
《人类简史》作者:若还有人对川普感到惊讶,就是自欺欺人
历史学家眼中当今如何应对全球变局的最优对策
川普许多举措我不认同,但背后的逻辑值得想想
胆小鬼游戏结束,认怂的川普怎么找到下台阶?
川普本身可能不算大问题。但他是未来大问题的先兆
真希望有人能拉住他。但愿人类这一次运气能好一点
秦晖剖析西方左派依赖身份政治,形成难以克服的恶性循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