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情緣 (短篇小說) 文 | 怡然
靜雯和靜雨是姐妹倆,她們只差兩歲。姐姐靜雯就像她的名字,文文靜靜,總是一副很成熟的樣子。妹妹靜雨則剛好相反,她天性好動,說起話來嘰嘰喳喳,如嘰珠落水,叮噹有聲。爸爸媽媽常常感嘆,你們倆的名字真是起得恰如其分,也真是名如其人哪。 靜雯那時正在B大學讀大四,她念的是中文系。靜雨在R大學經濟,那是她的第二個年頭。靜雯有個男朋友,也在B大,在讀博士研究生,他搞的是當時很熱門的美學理論專業。在學校的校刊上,經常可以讀到一位筆名叫殷實發表的文章,那就是靜雯的男朋友。因為大家殷實長殷實短地喊他,久而久之,反而忘記他的本名了。 別看靜雯人很文靜,可談戀愛算得上是前衛的。那還是大學二年級,在一次中文系舉辦的演講比賽上,她認識了殷實,倆人一見傾心。你要問靜雯喜歡殷實什麼呢?她總是嫣然一笑,不予作答。誰最知道靜雯的心事,自然是非妹妹靜雨莫屬了。每個周末,倆人回到家裡,悄悄話攢了一籮筐,白天當着爸媽說得不痛快。等到了晚上,姐妹倆把房間門一關,常常聊到深更半夜。搞得爸媽開始懷疑起來,心裡揣摩着,這姐妹倆是不是有什麼事兒瞞着我們老兩口呢? 在研究生班裡,殷實算得上是才華橫溢的一位。研究生還沒畢業,他已經和導師一起合寫了一部文學批評方面的專著。他觀察問題的視角獨特,自然也免不了標新立異。靜雯是個循規蹈矩的人,殷實的不安分,愛挑戰權威,熱衷於各種學術或政治爭論,令她心裡不安。唉,他腦子裡怎麼裝着那麼多離經叛道的想法呢,可她也知道,殷實是不會輕易接受她的那一套隨遇而安的人生哲學的。 靜雨和靜雯就是有那麼一點不一樣,她可不象姐姐,總是洗耳恭聽殷實的侃侃而談,靜雨是喜歡挑刺願意爭論的。為了某些哲學或美學問題,她和殷實常常爭得面紅耳赤,不亦樂乎。但唇槍舌劍的暴風雨過後,倆人還是跟兄妹一樣。有意無意之間,靜雨已經把殷實當成了自己的大哥哥,她是爭在嘴上,服到心底的。靜雨不止一次半開玩笑地對姐姐說:“哎,你可不要再抱怨他了,不然,我會把他搶跑的。” 對於靜雯的這個男朋友,她的父母是睜一眼閉一眼的。你若是讓他們挑一挑殷實到底有什麼毛病,他們還真挑不出來。但是老爸老媽總覺得有塊心病在那兒,什麼心病呢?原來靜雯的父母都是學哲學的,他們一直在R大執教。兩個人常常自我解嘲,搞了一輩子哲學,到頭來也沒折騰出個什麼名堂來。所以,他們真期望兩個女兒別再找學文的做女婿了,按照靜雯老爸的說法,就是找個工程師,過個踏實日子。 可人一旦墜入愛河,腦袋裡的那幾根筋還剩幾根聽使喚的呢?靜雯偏偏愛上了殷實,還是個未來的博士。靜雯的老爸禁不住長嘆,“唉,看來連改行的可能都不大了。” 在姐姐戀愛這件事上,靜雨是堅定地站在老爸的對立面上的。她經常批評老爸,“你懂什麼呀?以為學文科的人個個都像你們倆,整天乾巴巴地啃馬列康德黑格爾。人家殷實大哥是學文學批評的,專門去批評那些名家的作品,他的大作一見報啊,那反響可大了去了”。 老爸一聽,更急了,“那豈不是更糟糕了,批評對了倒好,要是一不小心捅到馬蜂窩,會饒上性命的,文革那時候死於文字獄的人還少嗎?”靜雨見老爸又動了真格的,就趕緊鳴鑼收兵,“得了得了,沒您說的那麼嚴重,看看你們的心態,都是被文革給害的,動不動就把性命抬出來,嚇死人啦。” 每當這種時候,靜雯總是默不作聲地在旁邊聽着,好象他們之間的爭論與她毫不相干似的。其實,她心裡早就打定主意了,只不過她是個孝順女兒,不想為這事跟父母吵翻。靜雯媽也看透了女兒的心思,私下裡就跟靜雯爸說,“唉,兒大不由爺,女大不由娘,只要孩子們自己覺得幸福,就依她們去吧。” 那一年的春天,風格外地大,刮得楊絮柳絮漫天飛舞,空氣幹得令人煩躁,好象註定了是個多事之春。殷實一邊忙着準備論文答辯,一邊馬不停蹄地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他和幾個談得來的同學成立了一個詩社,確切地說是個文藝沙龍。殷實大學的專業雖然是中國古典文學,但詩歌一直是他的酷愛,成立詩社也是圓了他多年來的一個夢想。他們經常聚會的地方,是坐落在新華大街上的一家米粉店。殷實很怪,他從來都不帶靜雯同去,儘管靜雯好奇,想去聽聽他們到底在討論些什麼。可殷實總推說詩社裡都是些男生,吵吵鬧鬧,喝酒胡侃,象你這樣的文靜小女生如何消受得了。 靜雯也很聽話,每到星期六,她就一個人乖乖地乘公共汽車回家了。靜雨開始看不慣了,她忍不住對姐姐說,“這象什麼話,大周末的,他一個人跑出去瀟灑,留下你一個人孤孤單單,這哪叫談戀愛啊?不行,我得找他說理去。” 靜雨是個急脾氣,她說去就去。從R大到B大,乘公交車只需要不到三十分鐘,靜雨就趁午休時間專門跑到B大,找到了殷實。一見面她就開口嚷嚷,“哎,殷實大哥,我想問你一句,你是在和我姐談戀愛嗎? 殷實被問愣了,“是啊,這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嗎?” “好,你承認就好。那為什麼一到了周末,就人影不見了?這對我姐太不公平了。” “噢,是為這個,我還以為天塌下來了呢。”殷實對靜雨是又喜歡又害怕,喜歡她的率真痛快,害怕她的辣利尖刻。“其實我不讓你姐去參加詩社的活動,的確是為她好,我怕她被我那幫哥們吵亂了腦子。” “得了吧,你以為我們的腦子全是豆腐做的,那麼容易亂啊。你這一說,我還非得去不成,陪我姐去,我倒是想去見識一下,看看誰那麼有本事,居然能吵亂我的腦子。好了,一言為定啊。”靜雨把長發一甩,跟完成了一樁偉大事業似的,準備去姐姐那裡請功去了。 當殷實和靜雯靜雨從米粉店走出來時,已經將近夜裡十一點了。詩社的這幫同學也都跟着撤了,因為末班公交車到十一點就收車了,要是趕不上,那就只好騎單車或是動用自己的十一號車架步量了。 一個叫阿寬的高個男生特意走到靜雨面前,很真誠地說:“下次我們有活動,你可一定得來呀,有你們姐倆參加,熱鬧多了。”靜雨白了那男生一眼,揶揄地說:“噢,你希望我們倆來,就是給你們湊湊熱鬧啊?” 阿寬趕緊辯解道:“噢,不,不,哪只是湊熱鬧,我是說你們也都很有思想,為什麼不來一起討論些問題呢?” “哈哈,你以為就你們有那個什麼‘思想’啊,長了個腦袋,哪個沒有點兒自己的想法呢?” “沒錯,沒錯,你這小丫頭,嘴真厲害,將來可夠我們殷實大哥喝一壺的。”阿寬悻悻然地走了。 殷實要送靜雯和靜雨回家,仨人騎着單車,在回R大的路上,靜雯一聲不吭,顯得心事重重,好象是在生殷實的氣。靜雨怕冷場,一路上說這說那。等到了她們家的宿舍樓下,靜雨搶先一步跳下自行車,沖姐姐和殷實說:“你們倆好好聊聊吧,我先上去了,困死了。”說完,打了個哈欠,三步並作兩步地往樓上跑去。 “這個機靈鬼!”殷實看着靜雨的背影,小聲嘀咕了一句。他回過頭來,見靜雯站在那裡沒動,也不吭聲。殷實感覺得到,靜雯是真的生氣了。“哎,別那樣,我又哪兒做錯了?” “唉……”靜雯嘆了口氣,“咱們去校園那邊走走,好嗎?” 倆人沿着校園的林蔭道慢慢地向前走着,“雯雯,別悶着,你對我有什麼意見就說出來吧,要不就打我兩下,解解氣。”殷實說着就去拉靜雯的手。靜雯把手一閃,她突然站住了,用兩隻手把住了殷實的肩膀,“殷實,你能答應我退出詩社嗎?” “什麼?退出詩社,這怎麼可能?我是創始人啊!大家還指望着我出點子呢。”殷實有些詫異。 “我以前一直以為你的詩社聚會只是談些文學創作方面的事,直到今天我才如夢方醒。你們真是離題萬里啊,尤其是那個激進的阿寬,還有那個假小子季宏紅,話說得那麼出格,我看早晚是要捅婁子的。”靜雯不無擔憂地說着。 “雯雯,你未免過於小心了。其實那有什麼呀,大家無非是暢所欲言,講了點真話而已。” “殷實,別人怎麼想我管不了,也不想管,可是你對我的意義不一樣。我不反對你參與政治,但不是這樣的做法,這太危險了。你就不為自己的前途擔憂嗎?眼看快畢業了,分配工作可是件頭等大事。再說,你不在乎你自己,你就一點也不為咱倆的未來想一想嗎?”靜雯說着說着,眼淚就流出來了。 殷實一下子慌了手腳,“別哭啊,雯雯,我答應你,以後詩社的活動只談文學,不談政治。這總行了吧?” “殷實,別哄我,人家也不是三歲的孩子。你真該從心底里反省反省了。” 倆人看來是談不攏了,只好暫且擱置起來。那次談話之後,靜雯感到他和殷實之間有了距離,殷實不再跟她談論詩社的任何活動,也很少提及他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倆人似乎心照不宣地躲開了某些危險話題。 殷實的詩社終於還是出了問題,正如靜雯所預料的那樣。出事源起於周末米粉店裡的爭論,阿寬和另外一個男生,爭吵得厲害,倆人又都喝多了酒,最終大打出手。那天殷實恰巧沒去參加活動,全部亂了陣腳。米粉店的老闆情急之下,給區派出所打電話報警。結果阿寬和那個男生被拘留了起來,派出所自然是通報給了學校,讓校方來領人。B大為這事還專門成立了調查組,殷實被傳喚過去,誰讓他是詩社的社長呢?校方認定這次事件的責任全在他,而且把他一手創辦的詩社給取締了。 詩社被勒令解散,殷實雖然免於行事處分,可那全是他導師四處奔波上下疏通的結果。不然,真的是不堪設想呢。這些都是小事,這次事件殷實損失最大的是,他失去了留校任教的機會。無論他導師怎麼去說和,別人都不買他的帳。系裡的某些人巴不得他搞出點醜聞,好趁機拔掉他這個眼中釘。 殷實很鬱悶,他故意躲着靜雯。他不是怕她埋怨,是怕見她幽怨的眼神。靜雯心裡很矛盾,出了這件事雖說是在她意料之中,但她沒想到會殃及到殷實畢業分配這件大事。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她爸媽這一次倒是出奇的開明,他們並沒有過多地指責殷實如何如何,還時常關切地詢問,怎麼老不見殷實來家裡一起度周末。靜雯很感動,看來天下也只有父母親是真正心疼自己的人啊。 靜雨看出了姐姐的心思,她很想做個穿線人,讓姐姐和殷實大哥和好如初。私下裡她就問靜雯:“姐,你真的那麼在乎殷實哥分配到哪嗎?要是他去不了理想的單位,你們就得吹燈拔蠟不成嗎?” 靜雯瞟了一眼靜雨,“唉,你還象個小孩子,哪裡知道咱中國的事。要是沒個好單位,你讀的書就白費了。一個讀書人,離開了正軌脫離了體制,就如同走進一條死胡同的大象,任你有天大的本事,都無計可施。” “姐,沒那麼嚴重吧。那你真就捨得離開殷實哥?你們原本是那麼卿卿我我相愛的呀!”靜雨迷惑不解地問。 “愛?我們是很相愛。可是,愛,不只是浪漫的事,也是世俗的事。如果不多想想俗的一面,將來倆人會更加互相折磨,痛苦的日子就不是一天兩天,而是一輩子了。” 靜雨瞪着亮亮的眼睛看着姐姐,好象不認識她了似的。二十年來,她還是第一次從另一個視角來看她的姐姐。她真的沒有想到,姐姐對殷實的情感竟是這麼淡這麼薄,淡得似水,薄得如霧。望着靜雯茫然若失的眼神,她悠然生出一絲憐憫。 
接下來的日子,殷實專心做起了他的博士論文,他要趕在五月底以前參加論文答辯。那個多事的春季,校園裡到處瀰漫着躁動和不安,有些系甚至允許學生停課去參加學潮。這一回殷實沒有盲從,而且博士論文有太多東西需要他潛心鑽研。他和靜雯已經有些時候沒見面了,倒是靜雨時常過來看看他。每到周末,都去圖書館幫他查閱資料,殷實一忙起來,飯都顧不上吃,靜雨就象貼心小妹妹似的,替他去食堂買飯。 每次一見到殷實,靜雨總忘不了說上一句,“我是受姐姐之命前來幫你,懂嗎?”殷實也就笑着問她:“那你姐自己怎麼不來呢?” “她呀,和你一樣啊,也在忙着趕論文呢。你們這些人啊,都是屬於現上轎現扎耳朵眼兒的人物。” “那你呢,是屬於先紮好了耳朵眼,時刻準備上轎子的人嘍!” 一句話,把靜雨說了個大紅臉。她舉起拳頭想打殷實,可拳頭停在了半空,她忽然意識到,殷實和她之間還是有段距離的,那段距離之間隔着姐姐靜雯。她也不是沒有勸說姐姐來看看殷實,可是靜雯似乎決心已定,她有意慢慢地疏遠殷實,從物理距離到心理距離。 殷實的博士論文終於有了眉目,那天晚上他心情特別好,推着單車送靜雨回家,這是靜雨盼望已久的了。倆人走在朦朧的路燈下,兩隻長長的影子時而交疊,時而分開。 走着走着,殷實忽然停下來問靜雨,“靜雨,能告訴我,你為什麼要對殷實大哥這麼好嗎?別忘了,他現在可是個落難之人啊!” 靜雨幾乎是未加思索地衝口就說:“因為我崇拜你啊!殷實哥。” “崇拜我?我有什麼值得你崇拜的?” 殷實目不轉睛地看着靜雨,靜雨避開了他的眼神,低下頭,小聲地自言自語, “嗯,殷實哥,其實崇拜是不需要理由的,我心裡一直都這樣想你的。”話一出口,靜雨就後悔了,她想起了姐姐,還有她那茫然若失的眼神。 靜雨抬起頭來,仰臉看着殷實,霎那間,倆人都愣住了。那游弋於他們目光中的是什麼呢?他們仿佛在熱烈地期盼着什麼,又在刻意地迴避着什麼。 殷實還是準備南下了,這似乎已成了他無法選擇的選擇。詩社事件使他留校的人生計劃化為泡影,他也努力去聯繫了一些研究所和報社,但都沒有結果。冥冥之中他感覺到有一雙無形的巨手,在背地裡操縱着他的命運,要想掙脫它,唯一的辦法就是離開京城,離開常人走的軌道。他現在也不得不佩服靜雯的預言能力了。 當靜雨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靜雯時,靜雯顯得有些落寂,她眼圈微紅地說,“唉,當初他執意不肯聽我一句話,才鬧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怪誰呢?” “姐,你去給殷實大哥送個行吧,畢竟你們曾相愛一場啊。”靜雯滿懷期待地看着姐姐。 “去送行,那不是徒然增加彼此的傷感嗎?還是讓他儘快忘了我的好。你對他比我還上心,要不然,你去送送他吧。” “姐,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呢?你怎麼能這樣說話?你,你太讓我失望了!”長這麼大,靜雨還是頭一次這樣批評姐姐,她從來都是個順從大姐的小妹妹。 殷實不願意讓任何人為他送行,他想一個人悄悄地離開北京,他不清楚自己的未來會是個什麼樣子,走一步看一步吧。列車就要啟動了,他有點悵然若失。是啊,他失落在這個城市的東西太多了,青春,愛情,還有許多他理不清的東西。 突然,殷實的眼前一亮,他定睛看了又看,確信他沒有看錯,是她,就是她!那個長發飄逸的女孩,那個長着一雙亮亮的大眼睛的女孩,急急地不顧一切地向他奔跑過來,手裡還提着一個紅色的網兜。她把網兜遞過來,放在他的手裡,大聲說:“殷實哥,這是你最愛吃的澳洲火腿,還有麻辣方便麵!”她幾乎是在喊。列車開動了,她就那樣小跑着向他揮手,她的兩頰緋紅,不知道是因為跑得太急,還是因為害羞。 殷實,這個很少流淚的男人,他的視線模糊了。靜雨的身影越變越小,直到完全從他的視線中消失了…… “我的小天使,我能給你什麼呢?”他從心底發出了一聲沉重的嘆息。 靜雯畢業後,如願以償地被分配到一家雜誌社當上了編輯。她也遂了老爸的心願,嫁給了一位工程師,心滿意足地過起了自己的小康日子。 兩年以後,靜雨從R大畢業去了上海一家報社,她想遠離北京,因為她想躲開姐姐,只要一見到靜雯,她便情不自禁地想起殷實。而她和姐姐最不能談的話題,就是殷實。 在靜雨的心裡,殷實是個值得女人去愛的男人,只不過那個女人不會是她,因為她也愛姐姐,姊妹之情是父母牽給她們的緣,是需要她一生一世去珍惜去呵護的。 不知道殷實在深圳發展得怎麼樣了,她刻意不去打聽,儘管偶爾還會想起他。可那又能怎樣呢? 就像穿越雲端南飛的大雁,除了陣陣啾鳴,表明它們曾經來過。人間有多少愛,不過如此,無論多麼轟轟烈烈,終是雁過留聲,了無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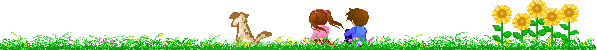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