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 红酒. 女人泪
舒怡然
搬到帕特家住,完全是个偶然。因为那时我很想回国,只剩最后一个学期了,临时找个落脚点而已。帕特独居的那间二层小楼,不大不小,好象是老天特意给我准备的。也因此结识了这位来自南美的老太太。所以人与人的相识,还真是有缘。
说起来,帕特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怎么太好。她的那张脸,不知道是哪儿出了问题,总给人一种凶巴巴的感觉。尤其是那双眼睛,好象充满了怨气,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迸发出来一般。
搬进她家的第一天晚上,我正在自己房间里收拾东西,帕特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来,她人很重,把个木板楼梯踩得咯吱咯吱直响。她在我房门口站定了,说:“怡,你知道我是一个人住这房子,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就剩我一个老婆子了。所以你来和我一起住,我很高兴。”说完,她呵呵地笑了起来。她这一笑,脸竟也变得生动起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看上去可爱多了。
可她的笑声嘎然而止,忽然板起脸,十分严肃地对我说,“怡,有一点需要有言在先,可不能往家里招男朋友,那不公平。你懂吗?”
听了她这半带胁迫式的请求,我几乎要笑出声来。帕特却满脸正经,她一点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依然认真地追问我,“你能答应这一条吗?”
我赶紧收起笑,也一本正经地回她,“没问题,答应你了!”
心里却在暗自嘀咕,哼,看来嫉妒真是女人的天性,不管多老了,妒心依旧啊。不过,象帕特这么坦白的嫉妒,倒叫我平生出几分喜爱。嗯,好一个性情中人,是我喜欢的那一类。
帕特属于那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她在联邦政府某部门工作,是搞城市规划设计的。她很努力,看得出,她不是那种干事麻利行动果断的女强人,动作总显得有点慢,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所以加班加点成了帕特的家常便饭,她经常是早出晚归,回到家已经是七八点钟了。
这倒为我们俩人共进晚餐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所谓共进,也就是共用一张饭桌子,其实还是各吃各的。她吃她的墨西哥饭,我吃我的中国饭,各得其所。
帕特爱喝葡萄酒,没有酒的晚餐,她简直就受不了。有时兴致来了,她便摆上两只酒杯,为我也斟满了一杯,并不由分说地要我和她共饮。在我看来,两个女人推杯换盏,无论如何都是有点怪兮兮的行为,所以就总是借故推脱。帕特并不在意我的婉拒,只要喝上酒,她便完全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酒醉话就多,帕特说得最多的就是她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并不令她满意,这小妮子不听话,早早地嫁给了一个银行小职员,读的四年大学全白费了。大概帕特觉得读书有个学位,也算是女人的一种资本。最让她自豪的是二女儿,她不光人聪明,拿了一个计算机的硕士学位,还在大都市纽约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最关键的是,她是个有主见的女孩,嫁给了一位大公司的高管,前途那就不用说了。帕特的婚嫁观,让我平生出一种错觉,她好象是出生在中国的二三十年代,被裹了脚的女人。
这些故事帕特不知道唠叨了多少遍,可每一次她都象讲新故事一样地新鲜,眼睛也格外地亮起来。“怡,你看看美国多好啊,我的老二才刚刚工作,就拿五万美元的年薪,五万啊,那可不是个小数字啊。唉,我自己虽然薪水不高,可我的假期多呀,好好享受生活的滋味,多难得。美国啊,真是给了我太多太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句话是帕特的口头禅。每次讲完故事,这便是她习惯性的结束语。
“美国给了我太多太多!”嗯,想想这话也有道理。尤其是对帕特这样的第一代移民,她体会得更多是美国的宽容富有,还有自食其力有劳就有得的社会规则。
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帕特也特别喜欢逛街。有几次,她约我一起去逛商场。每一次去,她都不会空手而归,总是稀里糊涂买回来一大堆东西,等下一个周末,又把一半的东西搬回商场去退掉。我笑她,看你累不累呀?她却乐此不疲地说:“嗨,你不懂,这叫满足购物欲。你看美国就是好,挣的钱足够花不说,花得也值。东西真是物美价廉。想想在美国,我们得到的真是太多太多了。”想不到,帕特的“美国给了我太多太多”,居然也包括逛街买衣服,外加随意退货。这一条可是无论哪个女人都喜欢的呀,帕特算是说对了。
令我困惑不解的是,帕特从来不提她的先生,这对一个美国女人来说,是有些怪异的事情。因为我所见过的美国太太们,多半是爱把先生挂在嘴边的。我暗自思忖,莫不是帕特的先生已经不在了。
有时,帕特会接连几天心情阴霾,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楼上的卧室里,谁都不理。这时的帕特,和那个谈笑风生爱讲故事的老太太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到底是什么惹得帕特如此抑郁?会不会和她先生有关系呢?偶然在地下室的沙发上,我看到了帕特的全家照,那大概是二十年前拍的。这是个看上去无比幸福的家庭。照片上帕特先生看上去很年轻,好象比她还要小几岁。两个乖女儿笑得无忧无虑天真烂漫。帕特对先生的事守口如瓶,这里面没准会有什么故事呢。端详着这幅全家福,我禁不住在心里揣摩着。
周五的晚上,帕特照例回来得很晚。她重重地把自己摔在客厅的沙发里。看她那疲惫的样子,我便轻手轻脚地往楼上走去。哪想到那边发出了轻轻的一句:“怡,能陪我呆一会儿吗?我很闷。”我把抬起的脚缩了回来,重新走回到客厅,坐在帕特对面的沙发椅上。帕特略带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站起身来,去厨房拿来了酒杯和一瓶还没打开的红葡萄酒。她用眼神询问我是不是来一杯,我摇摇头,她便给自己斟满了杯子。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星期五。”我有些木纳地看着她,不知她到底想说什么。
“唉,今天是我的结婚周年日,二十五年了。”帕特边说边喝下去半杯酒,她摆出了想喝个一醉方休的架势。
“那你先生他……?”我有点口吃,不知道该问什么。不等我说完,帕特就开口了。
“别提那个坏男孩了,噢,我的天,他可害苦我了。”说完这句话,她把剩下的半杯酒一饮而尽,接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我想拦她,可她把手摆摆,那意思是说自己没事。看来帕特是想给我讲她的爱情故事了,这会是个怎样的故事呢?
“我和他都是十几岁来到这个国家,我从墨西哥来,他的家乡是哥伦比亚。我们俩上的同一所大学,毕业后,我工作了,他继续读了法学院,他的志向是做一名律师。他聪明能干,如愿以偿地进了一家公司,开始了律师生涯。我们结婚了,你能想象得到吗?他向我求婚时,是那么虔诚。那时的我呀,每天就如同活在蜜罐子里似的。”
帕特说着,眯起了她的眼,仿佛沉浸在早已久远的甜蜜往昔之中。我也禁不住遐想起年轻的帕特,不象现在这么胖,苗条的倩影,与先生成双成对。那后来呢?我期盼的眼神鼓励着帕特继续说下去。
“怡,我告诉你说啊,这男人变起心来,那才快呢。”帕特似乎从梦幻中醒了过来,眼中那一抹温柔渐渐变得冰冷了。“唉,都是因为公司派他去法国分公司做法律顾问,才一年哪,一切就都变了,变了,变得不可收拾了。坏男孩!美国给了他太多的机会,连婚姻都是。”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帕特说抱怨美国的话。她又喝下去一杯,这一回,我可真得拦住她了,不然她要是醉倒在楼下,我怎么好把她抬到楼上去呀?帕特不肯听我的,仍然自顾自地喝酒。
“他离开家那一年,我们的大女儿才十一岁。人哪,真的很决绝。那一天,我就这样坐在客厅里,坐了整整一夜。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帕特唏嘘着,满脸是泪。
错?一段姻缘的结束,是对错就能说得清的吗?又怎么分得清谁对谁错呢?我默然。帕特又举起酒杯,红红的葡萄酒合着泪,她一饮而进。我起身把她从沙发上扶起来,劝她上楼去,因为我也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帕特踉踉跄跄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头便倒在床上。离婚的女人啊,结婚纪念日成了她最心痛的日子。
终于,我还是决定搬到公寓去住,不是嫌帕特的唠叨,而是我先生要来了。当我把这个消息兴奋地告诉帕特时,她显得有些失落,什么都没说。
搬走的那天,帕特去上班了。清早起来,我下楼来,见客厅的茶几上留了一张纸条,还有一瓶红葡萄酒。那纸条上写着:“怡,谢谢你在这儿,我们一起度过的好时光。没什么好送给你的,这瓶红葡萄酒是我去加州出差时买的,它是南加州的特产。你带走吧,和你先生一起喝。祝你好运!帕特”拿起那瓶酒,透过红红的液体,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女人所历经的世事红尘。
环顾一下这间小屋,又想起了我和帕特一起看中国春晚录像带的情景,看到相声小品节目时,她虽然听不懂,却也跟着我一起傻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把房门钥匙放在茶几上,轻轻地带上那扇门,两滴冰凉的东西从我的脸上滑落下来……
离开帕特那间小屋已经十几年了,可我还会时常想起这个南美老太太。算下来,帕特也该退休了吧。我不知道她现在的心情还好不好,是不是还在怨恨着她的那个“坏男孩”,是不是还常把那句话挂在嘴上,“美国给了我太多太多!”
发表在《世界华人作家》 2013 年第3期
《世界华人作家》是在国内发行的大型纯文学季刊,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和克鲁格出版社共同创办。它开辟了海外作家专栏,我的这一篇纪实文学就被刊登在此专栏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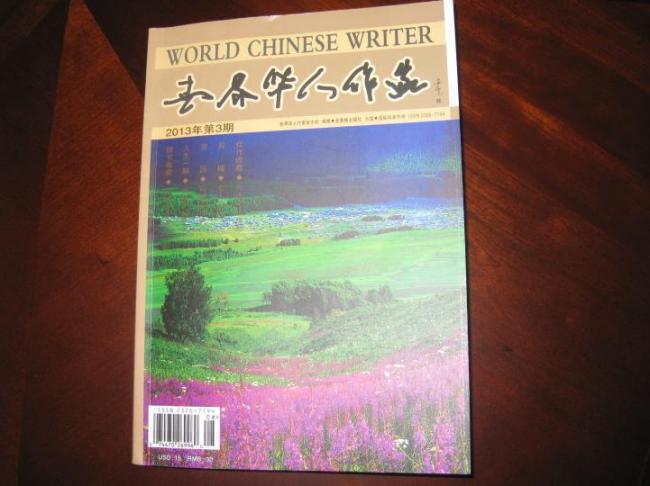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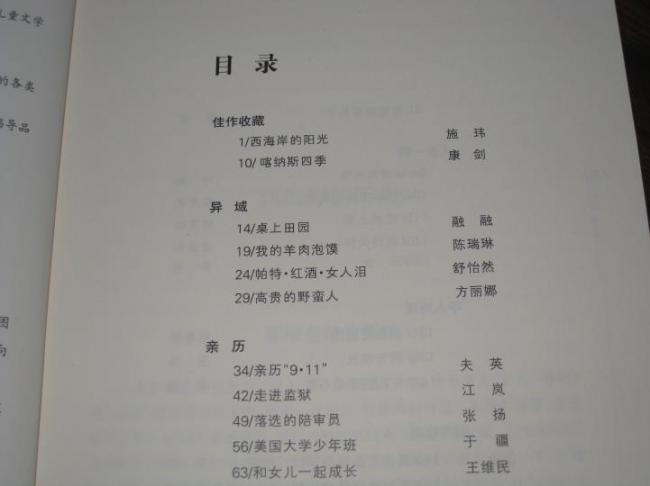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女人
“谁是我的妈妈?”(结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