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舒怡然 1 那是个很好的拍摄角度,科苏梅尔(COZUMEL)七个彩色字母,游轮,码头,大海,一个都没落下,全在镜头里。游客排起了长队,情侣照,全家福,欢快的靓男静女,蹒跚的老头老太,谁也不愿意错过加勒比海和煦的阳光,还有这瓦蓝瓦蓝的海。蓝得透彻,蓝得纯粹,蓝得让人心生浩瀚与悲悯。 正当我望着海水出神时,肩膀被人轻轻触了一下,“对不起,能请您帮我拍个照吗?”我回头一看,一位亚裔女人站在我身后,一副墨镜遮住了她大半张脸。我说,好啊,没问题。她喜出望外,“你是中国人哦,太好了。”她把手机递给我,转身快步跑向COZUMEL那一排彩色大字。她中等身材,穿着一条今年流行的白色休闲宽松裤。站在那几个字母之间,她踌躇了一下,大概是拿不定主意该为哪个字母站台。我说,“U”在正中间,可以照到全身的。她点点头,站到“U”字后面,做出这样那样摆拍的姿势,一忽儿如小鸟展翅,一忽儿又似金鸡独立,那件橘黄色夹克衫成了她手中的道具。我忙不迭地给她连拍了十几张。还是数码时代给力,让我这种不擅长拍照的菜鸟,也不至于丢人显眼。 我以为她该心满意足了,不料她却冲我喊道,“您再帮我拍几张不戴墨镜的吧。”说着,便摘下了墨镜。 就在那一瞬间,我呆住了。怎么……是她?这怎么可能?我用Zoom把她拉近,想看清楚一点。镜头里的这个中年女人,长圆脸,微黑,大眼睛有些凸,上嘴唇往外翘,咧嘴一笑,酷似玛丽莲 . 梦露。莫非真的是她,天底下有这么巧合的事吗?她似乎觉察出来什么,冲我说道,“随便拍几张就行,反正可以删掉的。”她快步走回来,接过我递给她的手机。当我们四目相视时,她愣了一下。 “你是,法拉利…?”话说了一半,我犹豫了,要问她吗? 她把墨镜重新戴上,好像根本没听见我说什么。“谢谢你啊,这游轮上中国人不太多,说不定咱们还会再见的。”然后,她扭头朝码头那边走去。离开船时间不远了,游客们陆续从科苏梅尔岛返回来。 我望着她的背影,十足的中年女人模样。窈窕身段没了,风姿绰约也没了,与我记忆中的那个“法拉利”太太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可是,你怎么能肯定她就是“法拉利”太太呢?没准儿是你看走了眼。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不过,关于“法拉利”太太的那些事,我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2 “法拉利”太太当然是有名有姓的。只不过,我们C大的这群留学生更愿意用这个绰号称呼她,似乎这才是她应该享有的名字。所谓名正才能言顺,就是这个意思。久而久之,她原本的名字反而被忘掉了。但是,我是没有忘记的。 第一次见她是在韩国人开的旅游品商店,暑期我在店里打零工。那是个闷热的夏日正午,火辣辣的太阳把沥青马路都烤软了,人也晒蔫了。刚刚送走一车亚特兰大游客,南方人可真厉害,三伏天也挡不住他们爆棚的购物热情。体恤衫一买就是半打,遮阳帽、阳伞、太阳镜、纪念币、冰箱磁铁贴,一股脑儿地往购物篮里塞,大有风卷残云之势。收银机嘟嘟嘟响个不停,老板帕克只顾喜滋滋地埋头数钱。我是负责打扫战场的,每次旅游大巴一走,整个店面就像被洗劫了一般。 这时,走进来一个女人,穿一件橘红色吊带裙,宽边墨镜,米白色高跟凉鞋,走路像模特走猫步,一条马尾辫在脑后摆来摆去。她直奔到柜台前,“嗨,又发财啦,瞧把你美的。”她的英语讲得倍儿流利,一听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那种。 帕克抬起头,推了推眼镜,“上完课了?要不要一起去吃午饭?” “当然了,这还用问。”她把墨镜摘下来,一双大眼睛,幽黑如点墨,上嘴唇俏皮地往上翘起,涂了浓浓的玫瑰红唇膏,冷艳如梦露。她的眼睛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什么。她定睛看见了我,便翩翩走过来。“哎,你是大陆来的吧?”她的口气居高临下,让人心里挺不舒服。我说,对,从北京来的。她把手伸过来,“认识一下,我叫萧莉,萧条的茉莉。”说完,自己先捂嘴笑了起来。 帕克走过来问,“你们认识?”我说不认识,这是头一回见面。她往帕克脸上拧了一把,“吃醋啦?什么都想知道。”帕克揽住她的腰,俩人纠缠着走出了店铺。店门口停了一辆红色法拉利跑车,他们钻进车子。萧莉坐在驾驶位上,引擎轰鸣,车一溜烟地跑了。 他们刚一走,墨裔老大妈玛丽娅就凑过来,“知道她是谁吗?”我摇头。她把手拢起来,凑近我的耳朵,悄声说,“老板的情妇,可厉害啦。”我白了她一眼,“你怎么知道的?”玛丽娅撇撇嘴,“天呐,哪个不知道,除了帕克太太。看她开的法拉利跑车了吗?那是帕克的。她不单帮他管两家门店,还替他管着体恤衫工厂,我丈夫就在那家厂里打工。她是正儿八经的二老板。懂吗?”我点点头,难怪呢,原来是一枝带刺儿的茉莉花。 从此,有关萧莉的闲言碎语便不绝于耳,喜欢编故事的不乏其人。那些故事的细枝末节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像电影画面一样逼真,由不得你不信。背地里留学生们都叫她“法拉利”太太,她时不时会开着那辆红色法拉利跑车,满校园逛游,惹人注目。 她本来的名份是赖太太,顾名思义,赖先生的老婆。赖先生在历史系做访问学者,挺老实的一个人,她是过来陪读的。来了没几天,人家就看出了门道。一个堂堂的访问学者,居然还不如餐馆大厨挣钱多。美国这地方,有钱才是王道,没钱寸步难行。她可不想安分守己地当赖太太受穷,她要出去找事做,去闯天下,去占领属于自己的码头。赖先生是位好好先生,只要太太高兴,做什么都行。正好她的陪读签证R2是允许工作的,就随她去吧。 她先去中餐馆做女招待,没干几天,就不耐烦了。这一小时五美金,得何年何月才能攒够买房子的钱呢?赖先生宽慰她说,急什么呀,等我申请到博士学位,一毕业就能拿到四五万年薪,还愁买不起个房子吗?她睁大眼睛瞪着他,可你得啥时候才能拿到啊?五年?十年?那太迟了。好像她心里已经有了既定目标,而赖先生规划的愿景,离她的目标十万八千里。 没事她喜欢进城闲逛。某一日,歪打正着地就走进了一家旅游品商店。店主是个韩国人,个子不高,戴一副金边眼镜,小平头理得齐整,眼神冷冷的,一副拒人千里的模样。他打量这个中国女人,像盯一个猎物似的,眼睛一眨不眨。她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忍不住发问,“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韩国老板冷冷地笑笑说,“看你漂亮,性感。有错吗?”在她不到三十年的人生经历中,还从没有哪个男人以这种挑逗的口吻跟她说话,连她老公都不曾这样。可是,她不但没有反感,反倒觉得刺激过瘾,就像用一根羽毛挠腋窝,心里痒痒的。开场白有了,往下的故事便接二连三顺理成章。 她先到帕克店里打工做售货员,一小时十美元,比之前翻了一倍。她窃喜,洋洋得意地对赖先生说,知道老板给别人多少钱?她伸出五个手指,五美金!赖先生狐疑地说,可是,我怎么觉得哪里不对头呢。咱可不能贪不义之财啊。她瞪大了眼睛,财就是财,还分什么义不义的,你啊,书呆子一个! 萧莉不比一般的女人,凡事她很少往负面去想,何必呢?要是处处循规蹈矩,那不是白在北京B大英语系混了四年。她曾不无得意地跟我说过,知道不,帕克一听说俺是B大毕业的,立马肃然起敬。他哪知道,俺对那劳什子游行啥的,根本毫无兴趣。说完,她放声笑起来,让人觉得没心没肺似的。 帕克的确很器重她,没多久她便被提升了,由收银员摇身一变成了二掌柜。其实就是帮帕克管账,打理开在城里的两家门店。萧莉有她的优势,英语好,人漂亮,性格泼辣,什么都不吝。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沉湎于“法拉利”太太的好梦里,如日中天,如火如荼。其实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最让帕克着迷的不是别的,而是她的“性感”。每次俩人开车兜风回来,帕克都是一副魂不守舍意犹未尽的模样。害得我们几个打工仔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当灯泡的感觉可不怎么样。萧莉一上位,连帕克先前的合伙人二老板阿金都被挤跑了。大概他也是受不了充当碍眼石的角色。 偶尔还会有人不识趣地喊她一声“赖太太”,她便顿时恼火起来。“赖太太赖太太,难道我没有名字吗?再这么赖下去,我可真成了赖人一个了。”人家便吐吐舌头,装作不响。心里却免不了嘀咕,发什么飙嘛,难道你不是老赖的老婆。 赖先生到底知不知道这回事——赖太太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法拉利”太太,我说不好。这样的危险关系能维持多久,谁也说不好。可谁也不愿意当那个戳破窗纸的人,大家似乎是商量好了,都守口如瓶,都不动声色,都在静等着看一场好戏。 3 游轮上的确是好戏连台,每天晚上各种表演闪亮登场,让人眼花缭乱。这是一艘最新推出的皇家加勒比号豪华游轮,它不像传统的游轮,更像一座海上移动的城市。从装潢精巧的步行街,到绿草如茵的中央公园,无处不彰显出设计师的独具匠心。因新冠疫情使它下水的时间一拖再拖。据说,就在一年之前,船上游客还是寥寥可数,如今却是人山人海。我和家人乐此不疲地穿梭于各个剧场。刚刚欣赏完花样滑冰,又匆匆赶去观看水上芭蕾,才走出脱口秀小剧场,又忙不迭地奔向皇家剧院看舞台剧。
可不管走进哪个剧场,我都忍不住左顾右盼,似乎是失落了什么,又似乎在期盼着什么。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裹挟着我,我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很奇怪的不安的情绪。希冀她会奇迹般地再现,那件橘黄色夹克衫,那个大眼睛翘嘴唇的女人。恍惚之间,我觉得她就藏匿在某个角落,一双漆黑如墨的眼睛正悄悄地盯着我。然而,奇迹终归没有出现。在一艘六千多人的游轮上,与一个人相遇的几率不比大海捞针高出多少。或许那只是我这个文学脑袋生出的幻觉,或许她与“法拉利”太太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我这么想着,透过玻璃电梯间,朝下面的中央公园看去。 电梯门打开了,一只轮椅伸进来,大家纷纷侧身让出地方。我扭头一看,怔住了,是她!她推着轮椅,身子很别扭地挤进电梯。她仰起脸,我们又四目相对。我和她距离如此之近,她眼角的一颗黑痣,脸颊上微黑的雀斑,脖子上的皱褶,一清二楚地映入我眼帘。一股酸楚的东西涌上心头,我冲她点点头,她没做任何反应,把脸别了过去。我低头看轮椅上的人,是个白人老头。一张布满老人斑的脸,看上去起码有七十多岁,几乎完全秃顶,只剩下几撮灰白头发稀稀落落地在脑后。放在胸前的一双手,不停地颤抖着。显然,他已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那双手了。这时,电梯门又打开了,她推着轮椅走向早餐大厅。看来,她已经打定主意,把我当陌路人,不想认出我了。 “法拉利”太太之后,萧莉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我一无所知。而撕破“法拉利”太太脸皮的最后一幕,时至今日,依然令我心怵。那时我和萧莉的处境完全不同。我有全额奖学金,不需要为牛奶面包发愁。周末到帕克店里打工,只是想挣个零花钱,也借机体验一下生活。留学生活好比一本书,校园里看到的不过是书的封面,书里的内容却是渗透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完全是文学青年的想法,天真浪漫得离谱,萧莉那时就是这么嘲笑和揶揄我的。我并不以为意。 那是临近圣诞节的某一天,天色灰暗,空气阴冷,一场暴风雪正紧锣密鼓地朝这座城市逼近。帕克店门庭冷落,生意惨淡。节日前人们都行色匆匆赶着回家,谁还有心思光顾旅游品商店。一整天都没见几个顾客,我闲得无聊,把柜台上的T恤衫翻来覆去地叠来叠去,为自己站在这里白赚老板的工钱而坐立不安。 萧莉看我无事忙的样子,呵呵笑起来,“嘿,大博士,快别瞎忙活了。是不是觉得啥也不干,对不起那一小时五美金啊?”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热,嗫嚅道,“嗯,没有没有,我是看不惯这台面上乱哄哄的。”她又讪笑,“你太善良了。放心吧,帕克一天不赚钱,这店也黄不了。”我有些诧异,心说,你不是他的合伙人吗,怎么还心存二意呢?她忽闪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诡秘地一笑,“瞧你,别战战兢兢的样子,咱们都是一个地方来的,难得有空聊聊天。你来店里快一年了吧,我们只是个脸熟而已,我还不太了解你呢。” 直到那一刻,我才认真地打量起眼前这个女人。她有着一张表情丰富个性鲜明的脸,算不上绝顶漂亮,却叫人过目不忘。从她黑黑的眸子里,你可以读出如水的风情抑或如火的欲望,你也可以读出小女孩的清纯和天真。这是个复杂多变的女子,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清楚的女人。大概看我半天没言语,她便自我解嘲地说,“好了好了,别紧张得像博士论文答辩似的。我知道自己这名声不怎么样,不过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认为,那是他们的事儿。哪个人没有本难念的经?我呢,还是我行我素。”说完,她拿出化妆盒,对着小镜子,描起眼线和唇线,然后抹口红,玫瑰红唇鲜艳夺目,与她的黑眼睛形成“红与黑”的对阵。 这时,店门打开了,一股西北风猛地灌进来,随后一位身穿黑色貂皮大衣的女人走了进来。她在门口站立了片刻,摘下黑色墨镜,然后缓步朝收银机这边走过来,齐膝黑皮靴发出咯吱咯吱有节奏的响声。我心里一沉,是帕克太太,她来干什么?我只见过她一面,那时还是夏天。 萧莉正对着小镜子专注地抹口红,直到帕克太太站到她面前,她都没有察觉。帕克太太伸出右手,敲了敲玻璃柜台,萧莉这才放下化妆盒,抬眼看着她。她们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火药味。我心怀忐忑地盯着这两个女人。 “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走人?” “走人?我没想过。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该去问帕克。” “哼,我让你现在就滚蛋。现在!”帕克太太伸出手,指向门口。 “笑话,你,你用不着吓唬人,我是给帕克打工,不是给你。我这就给帕克打电话。”萧莉伸手抓起了电话听筒。 帕克太太扬起手,把话筒打落到一边。萧莉拨开她,想抢回话筒。只听“啪”的一声,“不要脸的贱货!还赖着不走。抢钱,抢别人的老公,没教养的婊子。你给我滚!不然,我要报警了。” 萧莉捂住被抽红的右脸,站在玻璃柜台旁边,两眼死死地盯着帕克太太,好像要把她一口吞下去似的。我在店铺一角,被眼前的阵势搞懵了,不知所措。该怎么办?眼见自己的同胞挨了耳光,我就这么无动于衷吗?可萧莉暧昧地充当“法拉利”太太,到处张扬炫耀,私下里早就令大家所不齿,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她咎由自取,难道我还要为一个被千夫所指的人打抱不平吗? 萧莉回过头来,看着我,黑眸子里流露出的是一丝哀怨。慌乱之中,我急中生智,用眼神暗示她——赶紧走,快一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她似乎懂了我的意思。回过神来,快步走到店面后边的储藏间,拿上自己的双肩挎包,朝店门口走去。她推开门,但没有马上离去,而是转过身来,冲着帕克太太大声喊道,“你等着吧,总有一天,你会为这一切付出代价的!”说完,她扬长而去。那扇门在她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我再也没见过萧莉,她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我也没再回帕克的商店打工。后来,听说老赖去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去了。萧莉早就离开了他,他们之间恐怕也没了后话。 4 自从电梯间与那个女人不期而遇,我的耳边总在不停地回旋着当年萧莉抛下的那句话——“你会为这一切付出代价的!”或许,那不过是她愤然离场前随口而出的一句气话,她不会当真去兑现的誓言。回想起来,“为这一切付出代价的”反倒是她自己。一个虚幻的“法拉利”太太把一个活生生的赖太太推入了火坑。我们C大的留学生没有不替她惋惜的。你看嘛,丈夫即将要去攻读博士,自己在读金融硕士,明摆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却要去挖墙角当小三,何苦呢?也有人说都怪帕克这个混蛋,是他挥霍了她的感情,然后抛弃了她。可谁知道呢,即使她遇到的不是帕克,还会有马克、扎克,欲望与诱惑犹如一对孪生弟兄。 离开C大后,萧莉到底去了哪里,没有谁说得准。有人说她嫁给了纽约一个房地产大亨,住在曼哈顿的花园公寓,价值上千万。还有人说在赌城拉斯维加斯见过她,被一个阔佬揽在怀里,浑身珠光宝气,完全是贵妇人的派头。又有人说她嫁给了一个老头富翁,带她去了夏威夷。所有关于她的归宿,殊途同归。那就是萧莉嫁给了一个有钱人,活成了贵妇模样,圆了她“法拉利”太太的梦。这么说,轮椅上的老人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大亨、阔佬、或富翁。这就是她心心念念的“法拉利”太太的生活吗?我不知道,女人的心很难琢磨,而像萧莉这样的女人,就更难琢磨了。 游轮最后一天是海上航行,大船在南加勒比海上慢慢悠悠地漂游。我又信步走进游轮顶层高大宽阔的阳光厅,这里是成人专区,安静一隅,可也没有什么令人想入非非的节目。几个热水桑拿浴里,坐满了一门心思舒筋活血的老头老太。我不想去凑那个热闹,随便找了个舒适的躺椅,打开i-Pad,读书人到哪里都忘不了读书。环顾左右,大家和我一样,要么捧着纸书,要么刷着手机。 透过高大的落地玻璃窗,阳光尽情地倾洒下来。我凝神远眺大海,无法专注于书上的文字。有人从我背后走过,一股茉莉花的香气倏然飘过。我忍不住侧目。是她!那个熟悉的背影,白色休闲裤,黑色短袖T恤衫。我盯着她的背影,或许是我的目光有种魔力,她蓦然回过头来,我急忙从躺椅上坐起来。我和她近在咫尺,又是四目相对。她迟疑地走过来,在我旁边的躺椅上坐下来。 “你每天都来这儿?” “差不多吧。” “你好像一直在找什么人?” “噢,其实…,也没有,就是看着你有点面熟。” “不只是面熟吧。如果我说,我就是你要找的法拉利太太,你大概不会吃惊吧?” 她这么直截了当地戳破了窗纸,反而让我哑口无言了。 “哦,你…,这些年,你好吗?”我语无伦次地问。 她抬头看向大海,沉默了半晌才说,“也没什么不好的。你都看到了,我先生,也是我的合伙人,我们一起在纽约做房地产的。几年前,他得了帕金森综合症,病情倒是控制住了,但他无法再自己走路,只能坐轮椅了。” “哦,对不起,真是不幸。”我想不出该说点什么才能安慰她。 “没什么,我都想开了。毕竟我们也曾有过快乐的日子。我刚从C大毕业,到纽约去混,他是我的引路人。” “明白了,他就是传说中的房地产大亨。” “你们可真有想象力,还传说了什么?法拉利太太的日子可没那么风光哟。”她笑了,嘴唇翘起来,又像当年在韩国店时俏皮的模样。 “没有没有。老赖他…,他怎么样了?”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要打听老赖的下落。 她的笑僵住了,眼睛盯着窗外,“你,为什么要提他呢?我已经把他忘了。” “对不起,我不该问,他去斯坦福读博,就再也没了音信。” “可你知道,他是怎么去的斯坦福吗?”她转过头来看我。我摇头。 “是他高中时的红颜知己。你说,什么能敌得过一个女人的痴心痴情?他去找她,她把他引荐给了她的导师,就这么回事。我还没来美国之前,俩人就筹划好了。” 噢,原来是这样!是赖太太的徒有虚名,才导致“法拉利”太太的应运而生。听起来像是个玩笑——一个心酸的玩笑。 “那么说,他骗了你,可你,还是探亲过来了。”我问。 “也说不上骗。在美国,他的境遇变了,生存第一。他一个留学生,能有什么办法。那时候,他觉得来美国对我好,说能找到发展的机会。” “你可真够意思,这么宽容地去理解一个背叛你的人。”我说。 “说这些干什么,都过去了。我本不想告诉你的。我这顶法拉利太太的桂冠挺不错,反正想甩也甩不掉的。”她眼睛里闪着泪光。
我们沉默了。面朝大海。在海天相交的地方,隐隐约约地闪烁着山峦,楼宇,霓虹,还有人影绰绰,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她抹了抹眼角,“快看噢,海市蜃楼!”她的眼睛熠熠发光,那是我从未留意过的一种眼神,它留住了孩提时代的纯真与感伤。多么弥足珍贵,因为生活最终使人变得不再那么纯真了。 那个下午,我们就那样一起眺望那片遥远又绮丽的景象,直到它消失,看不见了。 翌日清晨,游轮靠岸。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又看见了她,推着轮椅,不紧不慢地朝码头走去。 本文首发《世界日报》小说世界专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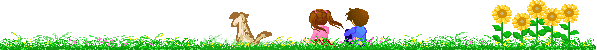
本文照片均由作者拍摄 怡然:重返伯明翰 (上) 怡然:重返伯明翰 (中) 怡然:重返伯明翰(下) 怡然:在消失的双子塔背后 《飘》下架了,一切会随风而逝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