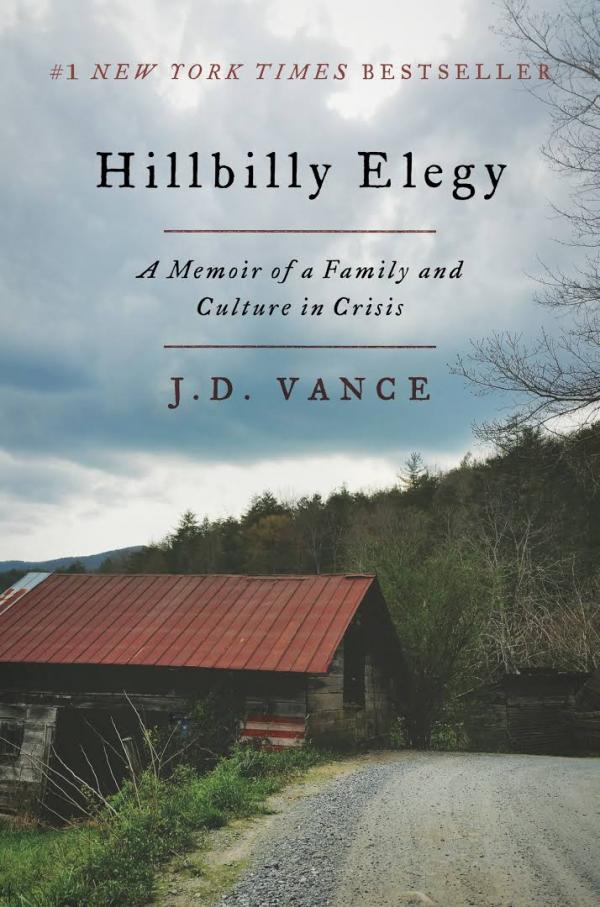下面是節選的這本書的章節
貧窮是家庭的傳統
我的家庭來自肯塔基州(Kentucky)東部山區,我們自稱為鄉下人(hillbilly)。把我帶大的外祖父母連高中都沒畢業,而我的整個大家庭里上過大學的人也寥寥無幾。各種各樣的統計都會顯示,像我這樣的孩子前景黯淡。我差點因為學習太差而從高中輟學,也差點屈服於身邊每個人都有的那種憤怒與怨恨。
雖然是白人,但我不會把自己等同於美國東北部信奉新教的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與之相反,我認為自己是蘇格蘭-愛爾蘭人後裔中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的數百萬白人工人階級當中的一員。
對於這個人群而言,貧窮是家庭的傳統。他們的祖先當年在南方當奴工,然後又曾當過佃農、煤礦工人,在較近的年代裡又當上了機械工和工廠工人。他們是鄉下人、鄉巴佬(redneck),或者是白色垃圾(white trash)。而於我來說,他們是鄰居、朋友和家人。
如果說種族是硬幣的其中一面的話,那另一面就是地理因素。當18 世紀的第一批蘇格蘭- 愛爾蘭移民來到新大陸時,他們就被阿巴拉契亞(Appalachia)山脈所深深吸引住了。這一地區固然廣袤——從南方的亞拉巴馬州(Alabama)和喬治亞州(Georgia)一直延伸到北方的紐約州一部——但大阿巴拉契亞山區的文化卻非常有凝聚力。
雖然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但定居在亞拉巴馬州的小漢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 Jr)在他那首鄉村白人歌曲A Country Boy Can Survive 中也把自己視作一名鄉下人。而當大阿巴拉契亞山區由支持民主黨轉而支持共和黨時,他們重新定義了尼克松之後的美國政治。但是大阿巴拉契亞山區的白人工人階級的命運看起來卻最為黯淡。從低社會流動性到貧窮,再到離婚和吸毒,我的家鄉成了苦難的中心。
毫不意外,我們是一個悲觀的群體,據調查顯示,白人工人階級是美國最悲觀的群體。需要指出的是,我並不是說我們這類人比其他人更值得同情,並不是因為白種人比黑種人或其他任何人種有更多值得抱怨的地方。拉美裔移民當中許多人面臨着難以想象的貧窮,但白人工人階級比他們還要悲觀。美國黑人的物質生活前景仍然落後於白人種族,但白人工人階級比他們還要悲觀。雖然真實情況中可能存在一些憤世嫉俗的成分,但現實是,相較於許多其他群體,像我這樣的“寒門”對未來更為悲觀,雖然很多群體明顯比我們更為貧困。這種現象就說明,肯定是金錢之外的地方出了問題。
工作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窮人家的孩子放棄了自己
當我提及我們社區的困境時,總能聽到諸如此解釋:“白人工人階級的前景確實惡化了,但你把本末給倒置了。他們的離婚率在增加,結婚率在降低,幸福感也在下降,但這是因為他們的經濟機會下降了。只要他們能得到更好的工作,他們生活的其他方面就會相應地好轉。”
我自己年輕時也曾這樣認為,它聽起來很有道理,沒有工作會造成很大壓力,而沒有足夠生存的錢會更有壓力。隨着中西部的製造業中心被掏空,白人工人階級不僅失去了自己經濟上的安全感,還隨之失去了穩定的家庭和家庭生活。
然而,那些艱難的經歷教給了我一點:這種關於經濟上不安全感的說法有其偏頗之處。幾年前,在我進入耶魯法學院前的那個夏天,我想找一份全職工作,以便攢錢搬到康涅狄格州的紐黑文(New Haven)市。我家一位朋友建議我在家鄉附近一家中等規模的地磚分銷公司打工。地磚特別重,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地磚搬到貨板上,為運走做準備。
這份工作雖不輕鬆,但一小時能掙13美元,而我正需要用錢,所以就接受了這份工作,並儘量多輪班和加班。雖然公司能提供如此相對穩定的環境,但管理者發現我在倉庫的這一職位很難找到長期員工。在我離開之前,倉庫共有3 名員工,雖然我當時只有26 歲,卻比其他員工年長許多。
其中有一名員工叫鮑勃,他在我之前幾個月剛剛到這個倉庫工作。他當時19 歲,有一個懷孕的女友。經理非常體貼地給了他女友一份接聽電話的行政工作。他和他女友的工作表現都非常糟糕。他女友差不多每隔兩天就要逃一天班,而且從不預先通知,而他則是長期遲到。不僅如此,他每天還要上3~4 次廁所,一去就是半小時以上。他的表現實在是太差了。
最終,鮑勃也被解僱了。被解僱時,他對着經理怒斥道:“你怎麼能這樣對我?你不知道我有一個懷孕的女友嗎?”而且像他這樣的還不止一個,我在地磚倉庫工作的短短時間裡,至少還有兩個人也丟掉了工作,其中還有鮑勃的表哥。
太多的年輕人對努力工作並不感冒,而好的工作崗位卻總是找不到人。一個年輕人有着各種需要工作的理由,如要供養未來的妻子還有即將出生的孩子,他卻丟掉了一份有着很好醫療保險的不錯工作。更令人不安的是,當丟掉自己工作的時候,他認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他身上就缺少一種主觀能動作用——他認為自己對自己的生活掌控很少,總是想要責怪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
重現19世紀晚期的工人與社會保險:令人震驚的工人傷亡率、工人的互助保險協會、大規模的移民潮、泰勒主義管理的興起、重塑自由勞動理念的鬥爭、歐洲的社會工程與美國的反國家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遭遇、進步時代勞動關係的政治經濟學。
那些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擔心的是中西部工業地區經濟的下滑,以及白人工人經濟中心被掏空。他們指的是製造業的崗位流向海外,而那些沒有大學學歷的人更難找到中產階級的工作。確有此理。但是,當工業經濟向南移的時候,老百姓的真實生活發生了什麼變化。在不利的條件下,人們用最壞的方式來應對,現在的美國文化在某種程度上越來越鼓勵社會的潰敗,而不是抵禦腐敗。
階層的文化烙印
童年的習慣仍在限製成功
實際上,我身上也有不良的習慣。那些幫助我順利度過童年的習慣在我長大後,仍在限制了我的成功。這就是窮困的鄉下人。一看到發生衝突,我就會逃跑或準備打架。而這對於我處理目前的關係中並沒有多大用處,但如果我小時候不這麼做,肯定會陷入家庭爭端的泥淖。
貧困家庭、工人階級家庭、中產階級家庭及富有家庭占有不同的資源,這種不同表現在日常生活中養育子女的點滴例行上,並有可能對孩子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實現美國夢的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現在有時候,妻子仍然提醒我,不是每次受到輕慢,如摩托車橫衝直撞地經過,或鄰居苛責我的狗的時候,都要跟人家幹仗。儘管我會衝動,但我每次都承認也許她是對的。
幾年以前在辛辛那提,我開着車和她一起,一個人搶了我的車道。我按響喇叭,那傢伙沖我豎起了中指。我們一塊兒在紅燈路口停下的時候(他在我前面),我解開安全帶,打開車門。我想要他向我道歉(有必要的話和他干一仗),但我的理智占了上風,於是我沒有下車而是關上了車門。
妻子非常高興看到我改變了想法,於是沒有朝我大喊讓我別像個瘋子似的(以前發生過),她告訴我她為我抵制住原始衝動而感到自豪。那個司機錯在侮辱了我的自尊,而我童年時所有的幸福感幾乎都是基於這種自尊的,自尊讓我遠離了校園惡霸的騷擾,讓我在母親被某個男人或他的孩子侮辱時給予她支持,自尊還給了我一些慰藉,無論多小都讓我感覺能夠掌控命運了。
在我人生的頭18年左右,中途退縮會讓我被冠以“孬種”“弱雞”或“娘炮”的名號。但我生命的大部分教會我做出理智、正確的決定,雖然這對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來說可能不屑一顧。於是那件事之後的幾個小時,我默默責備了自己。但這也是一種進步,不是嗎?總比用拳頭教訓那個混蛋如何文明駕駛而進了監獄好吧。
家庭的負重
“我身後的那個世界總能有辦法拉我回去”
我工作體面,住房無憂,愛情甜蜜,幸福地生活在我熱愛的城市辛辛那提,有了一個溫馨的小家,養了兩隻狗。我成功實現了向上流動,實現了夢想。至少外人看來是這樣。
但上坡路永遠不會平坦,我身後的那個世界總能有辦法拉我回去。母親又開始吸毒了。她從她第五任丈夫那偷傳家寶去買毒品(我猜是處方鴉片類藥物),而他則把她逐出家門。他倆在鬧離婚,她也無處可去。
我曾對自己發誓再也不管母親了,但我這個發誓的人自己卻變了。我仍在探尋那幾年前已經丟棄了的基督信仰,雖然很艱難。我第一次認識到,母親童年的精神創傷有多嚴重,也意識到那些創傷永遠沒有真正癒合過,對我來說也是如此。所以當我得知母親活得很糟時,沒有悄聲辱罵然後掛斷電話,而是主動要求幫助她。
美國和其他一些“發達”國家的“福利國家”政策,主要以補助貧困家庭收入為基礎,但這本書的建議是,社會政策也應當重視家庭資產積累,因為只有這樣家庭和社區才能持久地參與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我的計劃看起來非常簡單。我會給母親足夠的錢讓她能夠獨立生活,她會找個地方住下,存一筆錢領回她的護士執照,然後重新開始。同時,我會管着她的開銷,確保她走上正軌,用錢辦正事。這讓我想起了阿嬤和阿公以前經常制定的“計劃”,但是我確信這次會有所不同。
我想告訴自己幫助母親不是一件難事,告訴自己我已經學會正視過去,能夠解決自小學以來就困擾我的問題了,告訴自己既然我對母親的童年充滿同情和理解,我就能耐心地幫助母親戒除毒癮。
然而,我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在我對母親自作自受落得如此下場感到氣憤的時候,也會對她默默承受悲慘童年而深表同情。當我物質上比較寬裕,情感上心有餘力的時候,我會幫助她,滿足她的需要。但我也意識到自己能力有限,而且把錢給了母親或花時間陪了母親,我自己可能就沒錢付自己的賬單了,對那些我最重要的人也不那麼有耐心了,因此我更願意與母親分道揚鑣。我就在這樣的妥協下進退兩難,現在仍是如此。
人們有時會問我,我們能做什麼解決我們這群人的問題。我知道他們想聽到這樣的答案:一項神奇的公共政策或一個創新的政府計劃。但是這些家庭、信仰和文化的問題不像魔方那樣可以拼好,我也不認為會存在一般意義上的解決方案。我一個在白宮工作過的好朋友十分關心工人階級的困境,他有一次告訴我:“看待這個問題最好的方式,也許是承認你可能無法解決這些難題。這些問題總會存在。但是也許你可以從點滴做起,幫助邊緣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