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悲悯和感恩
虔谦
去台湾前,韩国同事问:“你去台湾,语言能通吗?”俄罗斯同事问:“那里的人会不会对你不友好?”我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不过我不怪他们。有些感受,也是我去了台湾以后才体会到的。
我是闽南人,我和台湾的全部因缘就从这里开始。泉州有个闽台博物馆,非常有想象力的建筑。那日因中途不适而没能进去参观。不过我想,那博物馆里不会展出往日安海镇小巷上凹凸的石条,不会有粉色的日春花,更展现不出说闽南话时人们脸上的那种神态。
儿时听奶奶唱“我爱我的台湾”。后来发觉这首民歌有点乡情以外的因素参入,但是我始终记得那头两句歌词:“我爱我的台湾啊,台湾是咱的家。”老人们说,台湾宝岛上物产丰富,米大,葡萄大,香蕉也大。听父亲介绍,他的亲三叔,我的三叔公,1949年以前去金门谋生,从此亲人两地茫茫。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了不起的三婶婆排除万难回乡寻亲,终于实现了两岸亲人的团聚。
这次去台湾,有些“蓄谋已久”,也有些心血来潮。
看外在,台北作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没有我想象中的“气派”,甚至可以说,我老家的县城晋江,市容上看都不会比台北差。但是有一样,就像台湾其他地方一般,台北的绿化非常好。那樟树不似橡树,苍翠灿烂胜似橡树。从台北南下的路上,我还看到久违了的木麻黄。木麻黄是儿时老家最常见、最蓬勃的树,后来由于各种开发,难得再见木麻黄的影子。
从台北到鹿港,我都没有外地人的感觉。除了自己的闽南人心态外,台湾乡亲没把我当外人是重要原因。我的闽南话讲得不溜,口音和台湾人的也不尽相同,很多时候我还是讲普通话。尽管如此,我见到的台湾人既没有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也没有任何的排斥。台湾人的友好我在来台之前就已经有所领略。我因为货币和行程的事分别给台湾的饭店和旅行社打了电话。接电话的人都非常的和善有耐心。等我亲临台湾后,从路边的清扫工到旅馆接待员,从小吃店老板娘到公车站的候车人,个个友好,让我感到一下子就融入其中。
感受一个接一个。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给我极大的震撼。我去台湾前,一位台湾朋友就跟我说:去台湾,一定要去参观故宫博物院,一定要去!去了台北故宫,我明白了他为什么那么强调。中国百万珍品,历经北南西东的几次大迁徙,终于在台安家。台北故宫博物院,以极为丰盛的文化内蕴和璀璨稀珍,平均每日接待上万参观者。导游在那里兴致勃勃地介绍,连唐仕女的装饰和当代日本服饰之间的渊源关系也不放过。整个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全然的、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
中正纪念堂和日月潭慈恩塔给我另一种震撼。中正纪念堂的蓝色华盖底下是高大的乳白色大理石楼墙,再往下是宽大的平台。我看着它,总觉得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后来才想起来,中正纪念堂的楼墙样式和中国长城的城关建筑(嘉峪关、居庸关等)酷似。不知当时是否有意建成这个样式,还是纯属巧合。关于这点导游没讲,介绍资料上也没讲。不过我想是与否,中正纪念堂楼墙类长城城关是冥冥中的某种必然。纪念堂建筑风格是中国式的,但它又没有传统中国宫殿的金碧辉煌,相反,它庄严、素朴、净洁、高远。蓝白相间是意料中的颜色,它以含蓄和清朗取代传统宫殿的咄咄之气。 “蒋介石是总统,不是皇帝。”导游说。
通往慈恩塔的山路郁郁葱葱,一派亚热带丛林的气息。蒋介石之母逝世于大陆,蒋公感到“收复”大陆希望日渺,无奈中兴建了这座慈恩塔来表达对慈母的思念和感戴。慈恩塔有着和中正纪念堂一致的格调:含蓄、朴素而又优雅。
鹿港是让我最感亲切的地方,这里是几百年前闽南人入台的港口。安海龙山寺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小时候常见人们到那里烧香拜佛请愿。鹿港龙山寺是大约360年前建的,也就是说闽南人几乎是一到鹿港,便开始了这项工程。漂洋过海的闽人始终怀揣着原乡的文化和信仰,把这个他们认定为吉祥的香火代代相传。在鹿港,我的脚触到了多年没有亲近过的熟悉石板,我看到了老家的粉色日春花。家乡样式的小巷,巷中是一户户的人家。那些红砖墙,那些中间镶嵌着细细栏杆的木门,屋檐下透露着阁楼的小窗,都让我童年的记忆油然复活。小巷中有一位心灵手巧的木工,他的木工制品(智力拼板、迷题等)多次获得台湾甚至国际奖项。这位木工曾参加过早期台海两岸的炮火对轰。那个时候,他在“那头”,我在“这头”;我对那些隆隆炮声记忆犹新。而今,“咱们有洞,他们打不到咱们。”他居然把我划成他们一边的!“现在好了,时代变了,我们两边都很安全。”他用闽南话对我说,我也不住地会意点头。到了鹿港,我觉得就像是到了家。鹿港妈祖庙前的热闹街区,小吃店小货摊密布,拿佛(番石榴)、蚵煎、米粉,各种地方特产四溢着台闽气息。
台湾文化处处充满着中国文化的要素,她映证了人之所言: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之外显得分外执著。日月潭里的文武庙,是这种文化执著的典型代表。1969年,中国大陆文革风刮正猛,台湾文武庙的重建却隆重开工。它模仿北朝殿宇格局,气势宏伟。入口处尽显辉煌,庙宇后端纪念孔子的大成殿则儒雅恢宏。登上文武庙顶,视野开阔,日月潭波光闪闪,景象秀美。庙内结构颇见匠心,特别是大成殿,迂回幽深,壁画相接,廊风清扬,喷泉声声,让人回味流连。导游说:武庙里年代相去甚远的岳飞和关公并坐,让人有些怪怪之感。我想这正是中国人信仰的执著处。由于在1999年的9.21地震中受创,当地政府又开始了文武庙的修建,热心人也在为此积极募款。
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那么积极的成分。闽南老家人们相当迷信。不管是佛陀还是道教高人,都被民间当作神来膜拜,导致许多庙宇里佛道合一。在南亚等地关羽也被当作有神力的偶像供了起来。在台湾短短数日我就见识了庙宇里烟萦雾绕,火熏炉黑。
在台湾,除了占主要比重的中国文化外,日本和原住民文化也处处可见。日本民族,从它的工业化和物质建设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民族的优良之处。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日本在台湾修铁路,客观上也有助于台湾经济和民生的发展。不过到了阿里山,台湾的悲情便在那大雾茫茫中显现了出来。阿里山极其珍贵的千年红桧巨树,被日本人砍伐殆尽。当年日本人在台建铁路,就是为了从台湾运去不易腐烂的红桧,拿它们来建造神社。导游告诉我们:“我们台湾现在不砍树!”也许这竟是来自阿里山的失木之痛!
再看日月潭,这个和阿里山齐名的台湾名胜,也落下了日本的痕迹。日月潭本为日潭和月潭,中间有该地原住民邵族所称的拉鲁岛为界。日本人在日月潭建大坝,潭中水位骤升,拉鲁岛几被淹没,只剩下一个头顶。日月潭文武庙的前身也是在那个时期因水淹而被迫迁徙。我想无论日本文化在台留下什么样的积极成素,阿里山的彻骨痛是很难从台湾的心灵中抹灭的。损人利己的残忍所造成的伤害不会因为一个所谓祭奠树灵的塔而消逝。
台湾有九个原住民民族,号称“九族”。其中日月潭的邵族只有不到三百人的人口。台湾政府对原住民文化采取了积极保护和发扬的政策。当然文化的相互渗透融合也是自然而然的,我经过邵族小镇时,发现邵族人大都已经会讲台湾话(闽南话)和普通话,饮食等习惯也在相当程度上和汉族融为一体。
除了汉文化的深厚根基外,日据时代的一些负面冲击和原住民文化的相对薄弱,都使得台湾人在岛上创立一种多元融合的独特文化难度加大。当初李登辉曾花大力气鼓动去中国化。几十年过去了,台湾的中华文化不烈,但依旧非常的浓。处在海岛的居民,常有一种岛民特有的自尊。台湾人在为生活也为自身争得尊重的各项打拼中,文化和归属的矛盾挣扎使他们趋于含蓄、内敛和坚强。我遇见的两个导游都非常客观地介绍台湾和大陆的文化连带和传承关系,同时他们又都显示出一种在原来的母国面前的不卑不亢。
台湾六天游,实际的旅游只有四天。我们从台北出发,走过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彰化等县,走过大概三分之一的台湾。所谓的“台湾走透透”其实并不难。一趟台湾旅游下来,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我的不少台湾朋友都跟我说过一句话:“台湾很小啦。”我也似乎明白了当年以摩西自比的李登辉为什么终于未能实现带领台湾人民“走出埃及”。李登辉自己的心胸没有开阔和柔软到足以使他真正理解台湾人民。台湾人民珍存着中华千年文化,那是他们的命根和血脉;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们又希望和中国大陆保持一定距离(距离说作为一种美学手段在中国古代就有,当然距离说作为一种人际关系形态却是现代才时兴起来)。台湾人民寻求作为一定的地域和社会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相应的和平、自由、特质和尊严。台湾的路就在这二者之间蜿蜒前行;台湾文化也就在这两者的结合中渐渐确立。
我游完鹿港后直接回台北准备返美。也许是因为鹿港是我本次旅行的最后一站,而鹿港和我的闽南老家是如此的合拍,进入美国移民通道时,我竟有二度出国的感觉!自从1989年首次赴美以来,我是第二次有这种感觉。这时我的心里充满感恩,因了台湾父老乡亲弟兄姐妹对故土文化的坚守,使我有实实在在的宾至如归的感觉,使我再次经历儿时的故乡。童年记忆中的一切在急速发展的老家已然逝去;而台湾,以她的宁静祥和,为我重现以往。
在国宾饭店门口等车去桃园机场时,由于是上下班高峰期,车左等右等等不来。耐不住性子的我显得焦虑不安。一位清洁工主动帮我去打听,告诉我这个地点没有错。后来来了一位三十五岁上下的中年男子。经一问才知道,他家住桃园,每天下午都在这里搭车回桃园。有了这位权威人士的确认,我心稍安。这位男士告诉我,他在这里最长时等了两个小时。
等车时我们颇聊了一阵,关于闽台,关于两岸政治等等。上车后我们坐的距离较远,没有机会再聊。我坐在那里,心想要是没有这位先生我不知道会跑哪里去搭车。想着想着感恩从中来。于是我掏出纸笔,写下了我的邮箱地址。等那位男子临下车时,我把纸条递给他,用闽南话告诉他:我要写信感谢你!
这趟班车的司机看样子三十几岁,个子很高。车内的标牌上写着他的名字。全名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李杰桧”。他的行车让我见识了什么叫驾驶技术一流。在上下班巅峰期,他驾着长长的公共汽车在各种车辆和摩托车流里穿梭,不时来回换车道摆脱滞留。有好几次我见公车和其他车之间的距离几近发位。他在似乎没有空间的地方硬挤出空间来行驶,否则这趟车不知要何时才能到达机场。中道下车的人们离车前都很有礼貌地和他道谢。他不太吱声,看上去有些神秘。我因为不熟悉停站的情况,所以用普通话问了一句:“这车到第二站台吗?”“到啊。”他也用普通话回答。
一个简短的对话,竟让我一时感慨。大陆人称“普通话”,台湾人称“国语”。两个名词都有内涵,有道理。天下的中国人,有了普通话,有了国语,它就是一家!
回到美国的第二天,我惊喜地看到了那位在台北车站一同等车的车友的来信!信中我才知道他的英文名叫麦可,他和大陆有许多货运方面的往来。
回公司后,我和同事说我在台湾不仅游山玩水,还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其中一位叫麦可。不料同事们就抓住这个麦可和我大开各种玩笑。一个问:“那你还支持中国出兵侵略台湾吗?”另一个说:“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
就像我走之前同事们所问的问题显示他们对海峡两岸的诸多无知一样,我回来以后他们的玩笑既显示他们的无知,也暴露出他们似乎希望两岸永远分离的奇怪心态。我不怪他们,毕竟水,没有血浓。在台湾,不管是看到那些勤快地为客人服务的餐厅小伙子,还是接触到那些为了售出特产而临时改说国语的小街居民,我的心都会涌上来一种同心、悲悯,一份亲情和感恩。爱他们,如兄弟姐妹,就自然会将心比心为他们着想。在通商打破屏障、信息连接全球的今天,政治的问题或许依旧无奈,但是文化和经济却是越来越显示出两岸间无界的难挡态势。我相信,国与不国会因为经济的互惠而显得索然无味,越来越归于虚拟;终究清晰实在的唯有文化和情感的一体和坚不可摧。我由衷相信这种一体会护佑着台湾人民的尊严、自由与祥和。(该文原载 《侨报》副刊, 2014年2月4日 ,有所删简;此为全文)

在阿里山三千年神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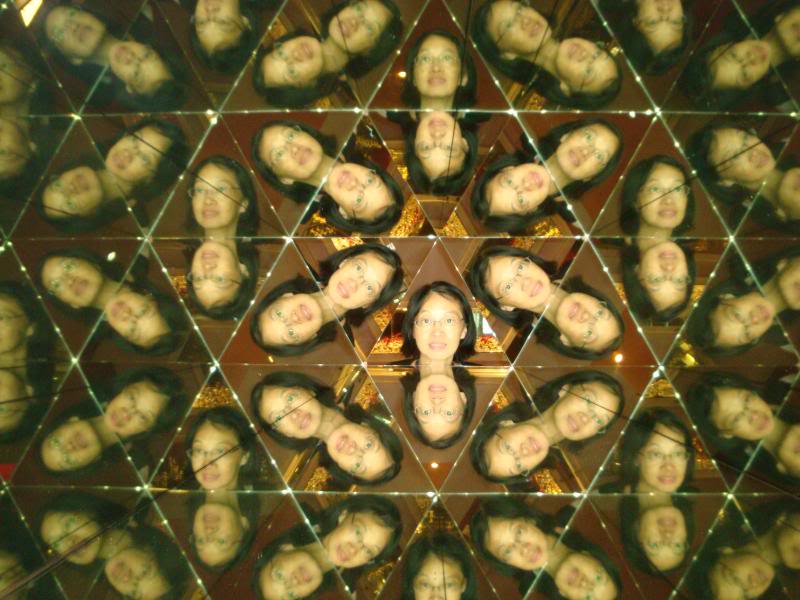
在一玻璃厂留下的特技摄影

清晨:从云品饭店俯瞰秀丽的日月潭

为台湾行而特意买的包。
鹿港,粉红的日日春
阿里山之歌 (外一首),诗组图
台湾游图片(三)让我倍感亲切的鹿港
台湾游图片(二)悲情阿里山
台湾游图片(一)
匆匆记下有关张灵甫的几个链接
“中国版阿甘正传”——新书上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