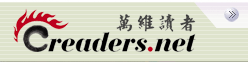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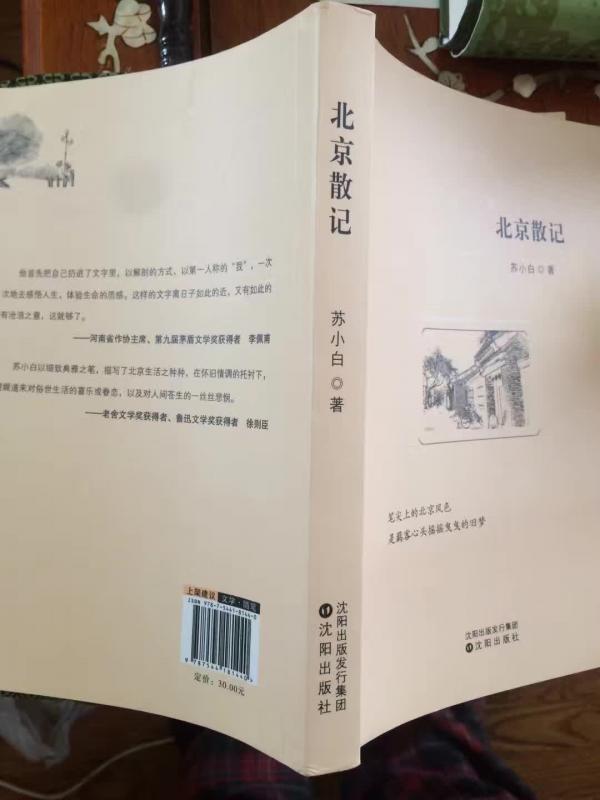
�
购书地址:http://product.dangdang.com/24229032.html
北京花市漫谈 ——摘自拙作《北京散记》(沈阳出版社出版)
昨儿,无意翻见到金圣叹的几句诗: 笑啼兼饮食, 来往自西东。 不觉闲风日, 居然头白翁。 这简单的四句诗并不见得好,读来却是亲切——大抵是因为我的日子原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一点偏爱吧。闲来算起,居住花市大街业已满五年了。五年来,刮风下雨,或风和日丽,天天来去这条街上,看着槐叶凋落复又爆出,看着垂花门下的人,门两边店里的花与路上急匆或散漫的行客,慢慢地竟是满头黑发添了白,心中的念想,也就淡了去。也是的,人这辈子,吃一些可口的茶饭,看一点好景,爱一个软和和的女人,知足了,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因此,决计要写这一篇文字的时候,先前对北京的那一点点抱怨,竟然一去无踪。 第一眼相中这片地方,还是五年前的夏日的午后。 那天我打车行至该处,一眼便被那一痕残破城墙和浓荫掩映下的繁华迷上了。这,恰是想往的京城,古意盎然,且又风流婉转。不大久,我就在此买房定居。其实,新世界与国瑞城的繁华,还是前些年才有的,明清时代的这一片地方,原是些手工业者定居之所,因为多是卖花儿的,便名为“花儿市”。《燕京岁时记》载:“花市者,乃妇女插戴之纸花,非时花也。” 可见,其时花儿市所卖之花儿,多是假花的。老北京人称假花儿为“像生花儿”。最初,这种“像生花儿”多为“通草花”,即为通草所制之花儿也。通草便为灯芯草,因茎体轻、空心,早年花匠就用此加工通草片,制成花朵。“京师通草甲天下”,说的便是灯芯草花儿吧。后来,造花原料有所发展,据《旧物文物略》云:“大体为二:曰绢类,曰纸类。绢类中有绫、绢、缎、绸、绒之分,纸类中有羊毛太、粉莲、通草及隔背之分。其造法有用模者,有用杵者,有用麻绳者。”一时间,花儿的品种与式样繁复起来。 老北京民俗:“姑娘爱花儿,小子爱炮”。 每每逢年过节,或走亲访友,或贺喜拜寿,姑娘与妇女们头上都要戴上花儿的,甚至连老太太的发髻上也要插朵小红石榴花,以取吉利,烘托喜气,所以,明清甚至民国以来,花儿市制售花儿的生意很好,热闹也就在所难免的了。清有民谣《花儿市歌》: 花儿市中多市花, 市花五色人前夸, 人来买花价不赊。 制花有匠极工巧, 枝叶纷擎出春爪, 一饭花中尽堪饱。 担花早起上长街, 千捆锦绣头街排, 护花高悬风字牌。 富家生女称国色, 一花三日插不得, 贫家无米愁炊烟, 女儿买花不惜钱。 可见,当年戴花之风多么盛。 然而,现时花儿市却鲜见制售花儿的了,偶尔有几家花店,也多是卖康乃馨、百合玫瑰等时令鲜花的。旧时文献中的上三条等等小胡同也早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华美的商楼与环境优美的住宅小区了。花儿市一条街上那两行古槐却是没除,春来秋去,枯荣自得,这正来得好,宛若妙女子,既有现代意识,也不乏古典情怀。在花儿市居家过生活,当然也是很妙。惹是想尝些老北京的阵年精炼的小吃,豆汁店、卤煮铺,有的,过花儿市不远便是;上好的烤鸭,也是有的,不必说离此一站地儿的前门全聚德,单是胡同深处那一家利群烤鸭店,便不知迷倒了海内外多少政商权富演艺名星。要说全国各地风味小吃,更不必跑远的,家门口的国瑞城和新世界商城均有各地名吃的排档,进去随便点,山西刀削面、陕西羊肉泡馍、过桥米线与新疆羊肉串,皆很便宜,又味道正宗。当然也有港台的各色各味,也有韩国日本风味,只要爱,尽管去。品茶、喝咖啡或饮酒,俗的雅的,高档如酒楼低档如小摊,也尽是有的,可以约朋邀友去,也可独自个儿闲来品一下,抿一口。至于穿的用的玩的,贵一点儿的成千上万,便宜一点儿也有几十元的,根据情况,由你消费。还有名医院,如同仁堂;还有名校,如文汇;还有名景点,如天坛;还有电影院,如百老汇;还有四合院,如曹雪芹故居、李莲英故居等,均散落于花儿市周边,闲来转一转、逛一逛,不能不说是方便。 小区里有小溪,小溪边有花树,花树旁有亭台。 每每春秋日,可以倚在阶上,手扶栏杆,看过往的肥女人,和铁篱上的花开了谢、谢了开;可以坐在窗前,看一天的流云在南来北往的燕背上聚了散、散了聚;可以坐在或荣或枯的草坪边,赏蝴蝶、听雀叫、看叶落叶生。夏月夜,可以坐溪边听蛙叫,可以坐石凳上数灯火,新虫与露水齐掉;可以亭下闲话,坛边散坐,不觉凉风习习,鲜草味与女人肌香齐袭,眼朦胧心也朦胧;当然,也可独个儿离去院落到大街边去,一杆杆灯下时有对弈的老者,或有读书的少女—— “夏日酷暑热, 街头人纳凉。 少女读书静, 童叟对弈忙。”(《夏爽》) 展眼冬天到来,下雪了,最好。揭去窗帘透窗一望,满院子里的树枝、栏杆与亭子,皆被厚厚的雪覆了,白白胖胖,浑浑圆圆,没有声音的,间或有人低着头走来,“咯吱咯吱”的踏雪声,腻满了一院子,宛若昨夜临家新妇房中的娇音。自然,不敢多听的,只须将帘子轻卷,晴明的雪光就浸进室内了,室内当然暖暖的,又有好晴光,人也清爽,读点诗看幅画,一个冬天就这样消磨掉,真是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