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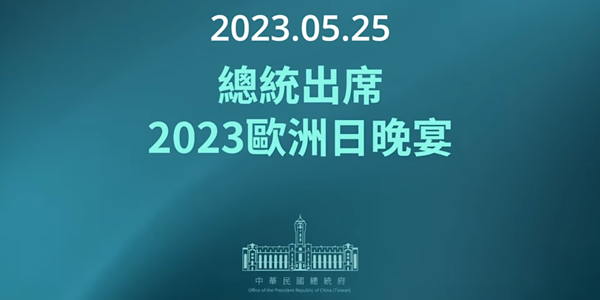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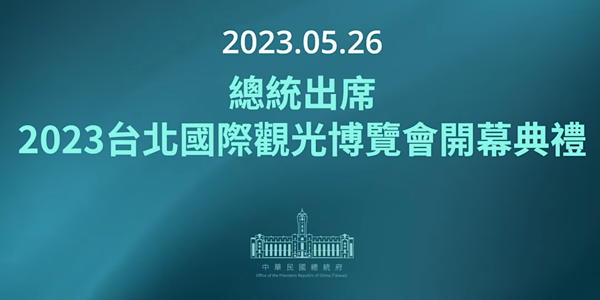




~~~~~~~~~~ 特朗普的自由城市和美国的伟大。 在停滞的时代,对美国独创性的积极愿景 保罗·INGRASSIA


也许现在影响美国的最大瘟疫是停滞的危机,它几乎弥漫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和技术到经济和文化的多样化领域,到整个国家的普遍弊病。虽然这些类别中的每一个都可能看起来无关,但统一它们的停滞源于一个共同的来源。他们复杂的起源充其量只能用一般术语来描述:官僚主义慷慨;“大众”或“现代”民主固有的系统性失败;精神沮丧的人口,精神上被毒品、有毒的食物、阴险的宣传和技术过度刺激所阉割。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不可逆转的,遵循一个文明的自然循环,一旦它转变为一个帝国,然后变得颓废,这时基本系统变得功能失调,整个机器——深陷于法律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过度复杂性——因自己的手工而内爆。
然而,即使走上了看似不可逾越的衰落轨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遵循了与其他过去伟大文明相同的模式,这些文明同样发现自己盯着被遗忘——总能找到更新的种子,无论多么小。虽然可能很容易忽视这些种子,特别是考虑到人们普遍存在的分心、对低时间偏好思维的敌意以及当今公众思想所特有的普遍无知,但那些能够约束自己以消除噪音的特别是有洞察力的公民,将因拼凑出一个致力于创新的乐观未来可能如何从衰败中走出来而获得回报。
首先,通过几乎每个重要重大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合法性的侵蚀,可以推断出指向目前似乎不可战胜的停滞的替代迹象:从政府,到主流媒体,到主要金融机构,到有组织的宗教,到娱乐业,到职业体育,到个人政治家,名人和商业领袖。如果现代社会每个支柱的合法性——即可信度——被迅速侵蚀,那么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将不可避免地崩溃——或者至少被改变(有什么替代方案?)。这表明社会契约处于终端混乱中。没有约束和创造一个民族的社会契约,社会必然会崩溃。
在我们的政治中,对一阶原则的分歧比比皆是:男人和女人是否不同;国家是否应该有边界;宪法,即土地的约束力和执行法,是否是一个可信和真正的权威(特别是在据称负责捍卫其戒律的律师中)。这些一阶问题中的每一个都应该清楚地证明,现在影响我们政治制度的疾病确实是恶性的,在旧规则下不能再忍受,因此必须经历彻底的转变或面临一定的死亡。除了阻碍我们当前系统根源和分支的政治两极分化,目前还没有人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外,我们货币体系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加上广泛地急于权力下放,似乎进一步暗示了摆脱当前疯狂的方法。最后,一般来说,州长和地方政治的相对力量在权力上只会增加,这与华盛顿现在可能存在的官僚主义停滞不悖,这应该进一步证明人们回归一种联邦主义、地方主义甚至部落主义,作为在联邦一级虚拟消除自由的潜在解药。
尽管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情况并不是忽视官僚、行政和深层国家代理人对联邦权力的巩固,这些代理人将后者的规则制定职责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过程中否认了民主部分——人民的意愿,从而有效地篡夺了国会的宪法授权。也不能忽视随着共同技术力量日益联系的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危险,这种技术有可能将区域区别完全平衡,并将公众同质化为集体蜂巢思维,人工智能的生存风险即将到来——切入公共话语的最低共同点——理论上可以在国家层面实例化并形成永久的官僚暴政,并且相当无缝地做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即使联邦权力在技术上或形式上相对于州权力有所增加,官僚主义慷慨和低效率的自然法则无一例外地困扰着任何规模过大的组织或系统,也应该为用更有效的州和地方替代方案来挫败联邦权力打开许多大门。在某些情况下,后一种情况代表了罗恩·德桑蒂斯在面对日益专制和非法的拜登政权时担任州长的最大成就。与此同时,它进一步强调了德桑蒂斯政府的悲剧,该政府现在显然关注的是追求联邦总统竞选活动——而不是以州长的身份探索一个创新的决策者可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华盛顿相对无能的界限,以追求由于法律主义和其他问题而在联邦和州层面都无法想象的项目。简而言之,目前,德桑蒂斯州长作为州官员(就此而言,任何红色州长)与他在等待被利用的政策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这座城市以其古老的版本,是政治生活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了超越部落社会的发展,在部落社会中,生存是政治的关键目标,并创造了一个统一战线,使包括艺术和科学在内的更高人类商品能够发挥其自然潜力。
因此,我们回到手头的话题:处于特朗普自由城市核心的机会。这项政策提案可能相当于特朗普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计划,如果实现,其决定性目标将成为他遗产的决定性标志。事实上,任何潜在的候选人都没有接受过比特朗普的自由城市倡议更明确基于美国伟大的政策,它提供了一个模板,真正的民主——而不是深层国家的宣传机构定期游行的天体伪造品,这些机构必须诉诸无耻的煤气灯、数字操纵和选举操纵来克服人民的意愿——可能会再次蓬勃发展。此外,该提案以一种与任何其他政策完全不同的方式抓住了特朗普的创业精神和创造性精神,并回到了他作为建设者和创新者的真正根源,近十年来,这一政策因一个诅咒独创性的整体系统的琐碎法律主义流血而悲惨地被边缘化。
自由城市的想法,至少在最普遍的水平上,作为自由和创新可以蓬勃发展的城堡,这引起了积极的古典和弦。它让人想起雅典和斯巴达等希腊城邦,它们成为民主实验各种表现形式的载体。这座城市以其古老的版本,是政治生活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了超越部落社会的发展,在部落社会中,生存是政治的关键目标,并创造了一个统一战线,使包括艺术和科学在内的更高人类商品能够发挥其自然潜力。古城是人类社会变得完全文明的地方,因此人类可以实现自己的应有目的。没有其他政治社会能提供人类在古城中取得的成就,这就是为什么最伟大的人类卓越模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仍然与这种政治形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城市充其充其经典替代品的极其粗俗的伪造品。就它与经典版本非常相似而言,它可能只是名义上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语义转变,这种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理解“城市”一词的基本指称。在古典时代,这座城市是小共和国——它是整个社会的政权,因此柏拉图最著名的对话的名字最大限度地充实了其意义。今天,这座城市是更大的政治挂毯的组成部分——它是大众民主政权价值观的孵化器。纽约、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等现代城市是政权意识形态的孵化器,也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过度行为最容易向其他人口展示的地方。因此,现代城市是社会其他成员最终将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好是坏)的政治预兆。
根据上述描述,现代城市的预测似乎相当暗淡。现在西方世界几乎每个主要城市的日常现实都只是为这种黯淡的预测增加了可信度:高犯罪率、无法管理的无家可归率、系统性的政府效率低下,使曾经的基本任务,如清理街道上的垃圾和人类垃圾,现在似乎是巨大的障碍。虽然这座城市(至少在目前的迭代中)可能在西方注定要失败,但现代城市并不总是一个失败的现象。非西方世界提供了几个高功能现代城市的例子,象征着西方国家城市的外观和运作方式。两个突出的案例是迪拜和新加坡,这两个城市应该因其创新和发展而受到赞誉,这些城市提供了西方领导人可能渴望的模式。令人遗憾的是,现代城市的破坏既是由于故意设计的,也是由于行政无能。因此,破坏的种子,将腐败制度化,同时剥夺其公民生存所需的基本保护,被烘烤到微积分中。 
非西方世界提供了几个高功能现代城市的例子,象征着西方国家城市的外观和运作方式。两个例外情况是迪拜和新加坡,否则应该庆祝这些城市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西方领导人可能渴望的模式。
然而,特朗普的提案似乎借鉴了美国以前最好的竞争独创性精神,因此可能会援引上述示范案例。出于这个原因,自由城市从根本上与当前代表整个西方世界城市的管理衰落哲学相悖。人们只能开始想象,一个城市没有受到官僚主义和监管慷慨解囊的可能性,而官僚主义和监管慷慨解囊,现在不可能建造另一座特朗普大厦,更不用说另一个曼哈顿了。如果允许美国创新精神在特朗普计划所设想的无监管的堡垒中不受阻碍地运作,那么可能发展的可能性只会受到人类想象力的限制。
人们只能开始想象,一个城市没有受到官僚主义和监管慷慨解囊的可能性,而官僚主义和监管慷慨解囊,现在不可能建造另一座特朗普大厦,更不用说另一个曼哈顿了。
这些城市也许能够将现代技术的成果与古代世界丰富的建筑传统相结合。想象一下,一个类似于原宾夕法尼亚车站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火车站,在20世纪60年代被拆除之前,但有高铁。以古希腊和罗马建筑为模型的图片库,或类似于中世纪大教堂的机场,而不是当今许多城市街道上令人心碎的残暴的怪物。这些城市也可能混合和匹配他们的主题,融合了每个文明的最佳风格。如果我们真的处于历史的尽头,而不是让过去压垮我们,我们应该从它多产的宝库中汲取灵感,融入每个文明中最好的东西,因为所有有记录的历史成就现在都触手可及,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完善他们的方法。这确实是一个文明的标志,它对自己的目标充满信心,并为自己的遗产感到自豪。例如,纽约,一个唐纳德·特朗普非常熟悉的城市,会充分实现其装饰艺术传统,继续在克莱斯勒大厦、帝国大厦和无线电城音乐厅的那些最高成就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而不是把这些遗产踢到现在正在建造的毫无生气的一维摩天大楼的路边。这些现代柱子看起来令人厌恶地陌生和不合适,并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这座城市永恒的天际线,使其变得难以辨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由城市将崇敬我们的神圣传统,提升而不是谴责人类精神,以及这种创新的神圣源泉,这不仅有利于艺术的蓬勃发展,而且有利于人类心灵的每一次伟大努力。
特朗普的提案借鉴了美国以前最好的竞争独创性精神。
自然界中没有基本法则说我们必须屈服于永远衰落。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制同质化的时代,但迫使我们遵守现状的不是在石板上从上面来到我们身上的东西,而只是一个人类习惯的问题——换句话说,选择。人类有自由意志和自由代理权:顺从的选择,也许是大多数人的偏好,不应该阻止少数人宁愿选择退出当前系统的人——并寻求一种替代方法来引导他们的创造力。这不应该被遗忘。没有理由让唐纳德·特朗普或埃隆·马斯克成为唯一能够追求其创业和创造性愿景的人。其他男人,甚至可能是更伟大的人,可能会在他们身后出现——推进他们开始的创新,或者发现一些全新的东西。如果自由城允许这些人追求这些才能,并将他们的天赋成果遗赠给我们其他人,那么整个社会将受益。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自由城将渴望复制古城的力量,这些世纪后,古城仍然是人类伟大的终极表达。因此,自由城的最终目标是恢复一种只有在古代世界才能实现的教育:即美德教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只有直接或间接地从这种文化源泉中催生了其他伟大的文明——无论是但丁的诗歌还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提琴的哲学——还是西塞罗的复兴,点燃了文艺复兴,激发了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并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为我们自己的革命提供了灵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自由城市应该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文化试金石——至少,也许是一种共同的语言,甚至可能是一个统一的宗教或种族。尽管我们的文明似乎与过去的文明相距甚远,但利奥·施特劳斯观察到,现代自由民主最类似于任何现代其他文明的古典民主。尽管面对普遍和同质的国家,这个命题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怀疑,现在以全球主义美帝国的双臂为代表,另一方面以中国技术新封建主义为代表,但秩序可能从混乱中产生的可能性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前景。文明的明显结束也可能提供新开始的种子,从创造世界国家的技术中也可能出现,使完全回归一种类似于古典时代的政治社区,这表明了我们独特的历史时刻的耐人寻味的可能性。 
即使在更普通的层面上说话,如果特朗普无法完全实现他对自由城市的愿景,他至少可能会想办法挪用联邦资源来资助艺术家制作电影和其他创造性的追求,以向世界展示他们的潜力。反过来,这些艺术家可以为自由城市可能成为一种娱乐性的方式为公众消费树立一个愿景——就像沃尔特·迪斯尼在20世纪60年代初计划Epcot时所做的那样。这将保持梦想的活力,并希望成为持续的灵感来源,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有一天可能会将自己带入生活。
Paul Ingrassia是两届Claremont研究员:他是2022年的Jack Roth慈善基金会John Marshall研究员和2020年的Publius研究员。Ingrassia先生于2022年毕业于康奈尔法学院。他的推特账号是:@PaulIngrassi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