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提要
为什么左派存在?它并不总是存在。直到现代,古代或中世纪的政治,或西方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了。事实上,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革命。有些人可能还想知道为什么右派存在,但解释左派也会解释右派,这是在左派诞生之后,并从那时起一直遵循它。
这个问题现在势在必行,因为在过去的四年里,左派几乎不受挑战地控制了美国,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紧随其后。为什么?如果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存在,我们几乎无法对抗左派的权力或推翻它对我们的霸权。 ~~~~~~~~~~
真正的天堂你能骂它是地狱, 真正的地狱你只能夸它是天堂。

美国不再像最初设计的宪法共和国一样运作。 中共已经购买了许多官僚主义的权力杠杆,并非常满足于允许拜登/奥巴马政权从根本上改变美国。
乔·拜登显然是满洲候选人,奥巴马显然是伊朗的选择。
这两个类似的独裁者之间的共生关系,造成了一个噩梦般的政治半机械人,旨在摧毁美国宪法,最初旨在弥补近几千年英国普通法的缺陷,并用可以想象的最好的政府来保护个人的生命和自由,以便他们能够追求符合他们最大利益的东西,而不会侵犯他人的类似利益。
归根结底,在摧毁美国宪法制度后,考虑到现任专制行政部门正在做什么,现在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有现行法律和SCOTUS的决定,但中共和伊斯兰教将不得不瓜分美国的战利品,中国对待伊斯兰拜登/奥巴马混合政权不可能与对待中国的穆斯林有任何不同。
对于那些认同恐怖分子哈马斯的LGBTQ哥伦比亚大学白痴学生来说也是。 就像1979年伊朗的学生帮助废黜沙阿并安装阿亚图拉一样,六个月后,他们要么什么都不说,要么在被处决时舌头被割裂。 ~~~~~~~~~~ 特朗普可能在2020年获胜,所以他在2024年获胜应该没有什么困难。然而,他会获得认证,还是荣誉将授予乔、米歇尔或漂亮男孩?这里的问题是民主党人使用的大规模选票收集计划。
让我明确一点:大多数民主党人不相信他们在作弊:他们只是在“赋予权力”。在他们看来,帮助人们投票是一项公共服务,即使它需要代表选民获得、完成、更正和运输选票。2020年选举期间,民主党人在威斯康星州公开这样做。
跟踪支出。确保边境安全。举行有效的选举。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让政府垮台吧。无论如何,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

我对不公正没有耐心, 对政府的无能没有容忍, 对辜负公民的领导人没有同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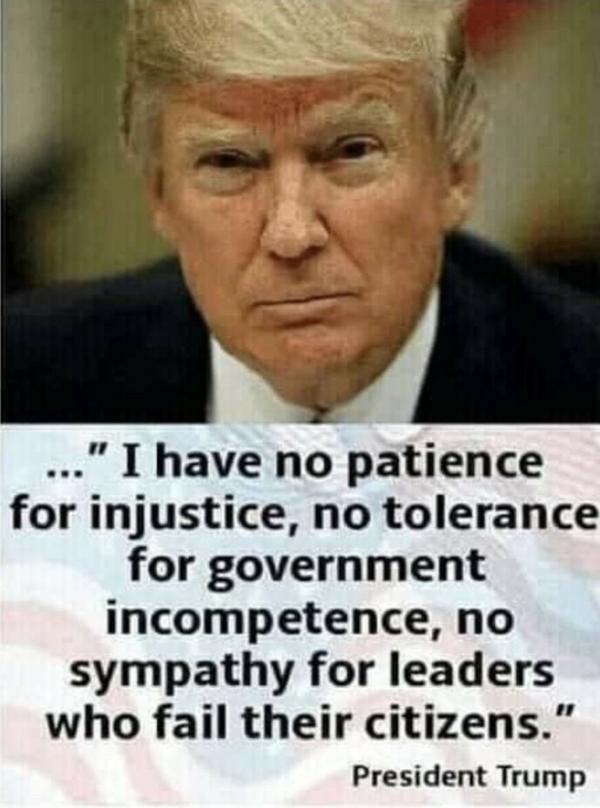
我代表我尚未选择的未来美国副总统,特此接受福克斯副总统辩论,希望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这是历史上第一所举办辩论的黑人学院或大学-日期待定。 我敦促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同意这一点。
让美国再次伟大!
我已经接受了反对歪曲的乔·拜登的第四次总统辩论,这次是与NBC和Telemundo一起。
作为共和党人,我们赢得伟大的西班牙裔社区很重要,拜登用严重的通货膨胀、高油价、街头犯罪和边境混乱摧毁了这个社区。
这次第四次辩论将与我们之前在CNN、ABC和福克斯上接受的总统辩论一起进行。
除此之外,我们还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Bret Baier和Martha MacCallum的邀请,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或弗吉尼亚州的另一个地点举办副总统辩论,稍后将命名。
这些是选民一直要求的辩论,这些是选民将获得的辩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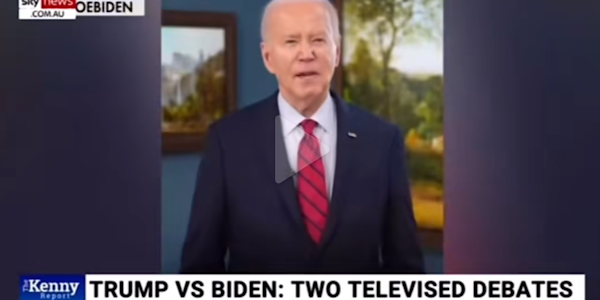
唐纳德.特朗普在2020年的两场辩论中输给了我,感觉他没有出现在辩论中。现在他表现得好像他想再次与我辩论,好吧,让我开心。伙计,我甚至会做两次,所以让我们选择一天的风格,我听说你周三有空……

这是一个15秒的剪辑,剪辑中有五个剪辑,他真的不能把一个句子串在一起!
那花了他一整天的时间,花了一整天时间来拍摄,那是他最好的一个,还是由五个剪辑合成的! 卧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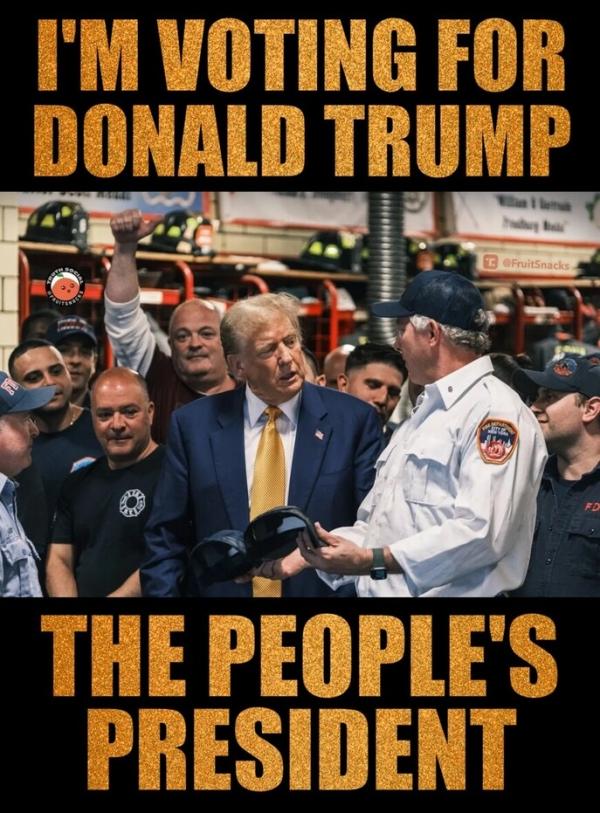




 ji ge shi ji ji ge shi ji
~~~~~~~~~~~ 为什么还有左边? 作者:Stephen Baskerville 2024年5月16日 
为什么左派存在?它并不总是存在。直到现代,古代或中世纪的政治,或西方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了。事实上,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革命。有些人可能还想知道为什么右派存在,但解释左派也会解释右派,这是在左派诞生之后,并从那时起一直遵循它。 这个问题现在势在必行,因为在过去的四年里,左派几乎不受挑战地控制了美国,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紧随其后。为什么?如果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存在,我们几乎无法对抗左派的权力或推翻它对我们的霸权。
激进政治的起源 传统智慧将政治激进主义与法国大革命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因为那是第一次世俗革命。但这并不能解释一种全新政治的出现。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第一次。第一次革命是在英国,它根本不是世俗的。它是由宗教意识形态驱动的。
左翼意识形态有时被描绘成一种世俗宗教,充满了自己的教条、异端和审论者。历史现实支撑着这种特征,因为世俗激进主义起源于宗教激进主义。
西方人不理解激进的宗教,即使我们发明了它。是英国加尔文主义者首先将宗教异议带到了发明现代革命的地步。一些美国人对宗教激进分子建立了后来的美国的想法感到不舒服——这是一个严重阻碍他们充分了解自己起源的盲点。清教徒开始在新英格兰居住,就在他们在旧英格兰的同志们正在进行世界第一次革命时。然后,他们的继任者鼓动在美国进行世界下一次革命,在数量上(并可能影响)远远超过我们作为“开国元勋”所崇敬的启蒙运动人物。
在这里,现代左翼和右翼之间存在沉默的阴谋,他们都不愿承认这一点。左派希望忘记其宗教血统,而右派不愿意接受基督教的激进过去及其在发明和煽动政治革命中的作用。
但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等式。它表明,左派意识形态的内容——已经改变到其发明者无法识别的地步——可能不如它创造的政治风格重要。它表明左派的存在不是因为它必然是对的。左派可能存在,因为它设计了政治方法,除了实际的不满之外,还有其他优势。也许这些方法更有效地实现了其目标;也许它满足了传统政治无法满足的情感和心理需求。不同的解释是可能的。同样,它打开了一种可能性,即一些左翼分子的担忧可能并非没有价值,但他们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手段可能会产生他们自己没有预见或意图的后果。最后,它开启了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左派并不总是存在,那么它可能有一天它将不复存在。
少数那些费心审查其祖先,即清教徒革命者议程的左翼分子,很难理解和同情它[2]——这比他们今天的激进伊斯兰主义更难理解和同情它。保守派在处理曾经被称为我们的“清教徒之父”时,几乎没有更多的感同身受。
在左边长大,我花了好几年时间试图理解他们,甚至开始钦佩他们。为了今天的目的,我想从清教徒那里吸取的一个教训是,左派在怨恨中茁壮成长。它不一定鼓励怨恨,而且指责左派的存在并不总是公平的。每个社会都有多种摩擦和怨恨的来源,其中许多从未被政治化。此外,清教徒花费了大量精力试图压制它。但左翼主义需要已经存在的怨恨,有时在压制它的过程中,也会控制、约束和引导它进入自己的目的。
我不否认一些怨恨可能是有道理的,我也不会说左派将其转移到某些目的必然是坏的。但冤情的优点是次要的。关键是方法:左派利用并组织怨恨成为意识形态、革命和类似手段来实现其目标。
右派拒绝左派的议程,并声称要抵制它,但它经常模仿他们的技巧。结果是一种事实上的勾结,左派的假设在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进入了我们的政治和文化。
右派被抛在后面 几个世纪以来,左派多次改变形式并重塑自己——从宗教到共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最近的性。 当然,左派取得了成功,其中一些是应得的。
但它也善于在失败中幸存下来。 它的不满不断更新,失败使其不受阻止。 如果我们不能改革教会政府并消除偶像崇拜,也许我们可以消除贫困,如果这行不通,我们可以解放妇女和有恋物癖的人。
有些人总是愿意宣布“左”和“右”的称呼已经过时,我们已经达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 这种声明总是为时过早。 当然,左翼和右翼的元素往往都准备忘记他们的原则,并与对方勾结。 但这与使这些原则过时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今天发生的事情最好理解为不是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两者之间的又一次勾结。 但勾结不是对称的。 左边总是领先,右边跟着。
毕竟,左派在反对派中茁壮成长,当他们参与“斗争”的浪漫时,他们最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原则。
当他们最有可能抛弃这些原则时,是当他们开始闻到成功的甜味并掌权时,正如乔治·奥威尔对动物农场的猪所描述的那样。 我们今天生动地看到了这一点,因为左派分子成为他们曾经鄙视的富豪和军国主义者,甚至是种族主义者。
相比之下,右翼认为反对派令人反感,很少表现好;右翼人士更喜欢掌权,他们最杰出的领导人通常享有权力和财富。 他们最有可能放弃他们的原则,不是在他们成功的时候,而是当他们像现在一样不成功和挥杆的时候。 当左派获胜时,右派会变得不自信和软弱,并羡慕左派的成功、权力和财富。 那就是右派想跟上并分享左派的成功时,它会找到任何借口来做。 当时的右翼——特别是建制派右翼,在它创建的组织封地内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寻找机会在左翼精英中讨好,并妥协其原则。
简而言之,当右派占主导地位时,左派和右派都最有可能违反原则行事。 这是我们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存在的默认位置,至少是一种明显和相对稳定的状态。 相比之下,当左派占主导地位时,双方最有可能出卖他们的原则,以享受权力的陶醉。 这是滑坡,我们现在正滑入暴政和破坏。 我们没有迹象表明知道如何扭转它。
这把我们丢在哪里了? 毫无疑问,左翼意识形态持续了几个世纪,因为它不断从年轻人的队伍中喂养。 再加上年轻人逐渐增加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更大趋势,似乎左派的胜利就是清教徒所说的:命中注定的。
叛逆政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几乎不需要解释。 需要理解的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可能标志着左翼和现代政治的逻辑结论。 在这个阶段,不仅左翼政治的叛逆风格,而且其内容也有助于招募青年。 这涉及性政治对左派的统治,家庭和儿童被故意政治化,以解放和“赋权”,首先是妇女(以及同性恋和变性人等准和伪妇女),然后是儿童自己。
我在其他地方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描述,不会在这里详细说明。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创新是从社会和经济不满转变为激进左派先锋的性不满。 这也是最难理解的。 底线是,大量儿童现在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实际上没有任何父母权力或家庭结构来文明、管教和培养他们,使他们融入稳定的社会和公民秩序。 鉴于叛逆和性行为往往在大致相同的年龄出现,性政治为青少年提供了一种特别诱人和爆炸性的组合,使其无法控制,这并不奇怪。 他们对最极端的左翼意识形态的易感性使他们渴望摧毁文明秩序的每一根支柱,以及他们自己,以意识形态的名义肢解自己的身体。
他们在美国掌权的政府植根于这种意识形态,并鼓励自我毁灭。 但最令人沮丧的是,即使是反对派——共和党、保守派压力团体、律师事务所、智囊团、媒体、大学——都对如何反对这一点不理解,大多数人甚至害怕它,甚至无法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上述原因,有些人甚至在推进它时加入了自己的声音。 性激进主义比以往任何左派议程都更能压制自己的反对意见。 它甚至使那些最想赞美“男子气概”的人女性化和幼稚化。
除了这个,回收种族或阶级政治的左翼运动并不重要。 今天明显的种族战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幌子,一个侧翼行动,以转移人们对左翼真正尖端议程的注意力,即性。 毕竟,黑人的生命很重要是黑人女权主义者的创造和运作,对福利、平权行动和赔偿的持续要求对黑人男性没有任何好处。 相反,她们赋予黑人妇女权力,在政府的“援助”下,使男性无所作为,并剥夺了男性作为提供者、保护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性左派把我们带到了意识形态政治的荒谬,将工人阶级男子和中下层阶级家庭作为“压迫者”,并宽恕对儿童的肢体切割。 可能会有更多的变化,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足够的东西,意识到文明的生存需要我们完全放弃意识形态政治。
除非我们冒险走出我们的舒适区,放弃令人放心的幻想,并停止试图通过遵循最初背叛我们的愚蠢习惯和无能的领导人来摆脱极左派的控制,否则这是无法做到的。
Stephen Baskerville是华沙Collegium Intermarium的政治研究教授,也是《不是和平而是一把剑:英国革命的政治神学》(Routledge,1993年;Wipf & Stock,2018年)的作者。 自2020年初以来,他关于美国政治的书,为什么会发生? 为什么美国会“共产主义者”来自Arkto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