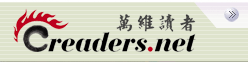� 彭运生解唐诗(18)
司空曙 1、喜外弟卢纶见宿:“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以我独沉久,愧君相见频。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 有言外之意的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不管愿意不愿意,“树”必须经受“雨”的浇淋,“树”也不能让自己的“黄叶”变成绿叶。夜晚降临,“人”却可以让自己克服黑暗,因为人有创造性,通过创造出“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另外,人既然可以创造出灯以克服黑暗,也就有可能创造出可以改变自己“白头”的东西。创造性让人用不着对命运逆来顺受。 “创造性”受到了隐秘的肯定。 2、江村即事:“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系”的意思是拴住,“正堪眠”的意思是“正是睡眠的好时候”。 如果说我们在“正堪眠”的时候去睡眠是一种享乐,则我们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享乐,因为这样的享乐只能发生在“月落”时的“江村”,只能发生在我们“钓罢归来”的时候;享乐需要时间上的保证,而适宜于享乐的时间容易被其他一些必需的行为所占用,譬如如果我们在船上睡眠的时候不能保证“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也就是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我们入睡之前就必须“系船”。 “享乐”受到了隐秘的肯定。 皇甫冉 1、舟中送李八:“词客金门未有媒,游吴适越任舟回。远水迢迢分手去,天边山色待人来。” 有言外之意的是“天边山色待人来”。 “山色”美好,却又是远在“天边”——要想欣赏山色,我们首先必须长途跋涉,总之,美不是垂手可取之物,欣赏美也不是简便易行的事情;其次,山色抱有一个目的,表现为“待人来”,所以,我们去亲近山色,与其说我们从中得到了美的享受,不如说我们成全了山色的心愿,欣赏美还是一种利他的行为。 “观赏风景”受到了隐秘的肯定。 2、题裴二十一新园:“东郭访先生,西郊寻旧路。久为江南客,自有云阳数。已得闲园心,不知公府步。开门白日晚,倚杖青山暮。果熟任霜封,篱疏从水度。穷年无牵缀,往事惜沦悮。唯见耦耕人,朝朝自来去。” 有言外之意的是“果熟任霜封”。其字面含义是:果实成熟后,再遭受什么样的霜打都无所谓了。 对于果实来说,最安全稳妥的是早熟,因为霜降有可能提前来临,这是未成熟的果实所不能忍受的。 “早熟”受到了隐秘的肯定。 3、问正上人疾:“医王犹有疾,妙理竞难穷。饵药应随病,观身转悟空。地闲花欲雨,窗冷竹生风。几日东林去?门人待远公。” 有言外之意的是“窗冷竹生风”。 “窗”户寒“冷”,竹子就一反常态,居然“生风”,风将加剧窗户的寒冷。总之,寒冷会引起世界的混乱,让万物背离自己的本性,终至于越俎代庖,寒冷本身将变得更加寒冷,恶性循环。 “寒冷”受到了隐秘的否定。 4、泊丹阳与诸人同舟至马林溪遇雨:“云林不可往,溪水更悠悠。共载人皆客,离家春是秋。远山方对枕,细雨莫回舟。来往南徐路,多为芳草留。” 有言外之意的是“离家春是秋”。 有了家,我们就有了自由。现在是春季,如果我们想感受秋季,我们再也用不着等待秋季按部就班地来临,而是简简单单地离开家。 “家”受到了隐秘的肯定。 5、送朱逸人:“时人多不见,出入五湖间。寄酒全吾道,移家爱远山。更看秋草暮,欲共白云还。虽在风尘里,陶潜身自闲。” 有言外之意的是“移家爱远山”。 “山”和“家”的距离必须足够远,才能激起我们的喜爱之情,因为我们爱的是“远山”。让家和山的距离足够远,有两个方法:让山不动,移动家;让家不动,移动山。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可取的是“移家”,因为移山难于移家,这是因为山比家更为巨大。总之,家因为相对弱小就必须被搬迁,即使家本身不希望自己被搬迁。 “弱小”受到了隐秘的否定。 慧能 弘忍大师准备传衣钵,就让手下的和尚写偈语,看谁学佛的体会最深刻。“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是神秀上座的偈语。行者慧能的偈语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大师把衣钵传给了慧能。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字面含义是:菩提树和明镜台从根本上都是不存在的;“本来无一物”的字面含义是:所有的事物从根本上都是不存在的;“惹”的意思是沾染。 “本来无一物”呈现为一条哲理,是对万物本性的一种概括,意思是:万物归根结底是不存在的。慧能的偈语不是在宣扬这一哲理,而是在歌唱这一哲理:有了哲理,慧能就可以轻松地反对神秀的各种说法——“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是只需把这一哲理运用到“菩提树”和“明镜台”二事物就能轻松得出的结论;有了哲理,慧能可以让自己的对手神秀显得愚蠢、荒唐——把“本来无一物”运用到“尘埃”身上,则“尘埃”从根本上是不存在的,这么一来,自然也就谈不上“惹尘埃”了,神秀说“莫使惹尘埃”就相当于说“不要让石头夸夸其谈”。 慧能的偈语体现出来的,是慧能的诗才。慧能最终继承了弘忍的衣钵,成为禅宗的第六代祖师。禅宗是诗意浓郁的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