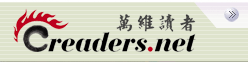�悖论的实质是文学
悖论问世之日,即是人们力图解悖之时,因为对于我们的常识和理智,悖论都是一种压力,我们因此而有了莫名的痛苦。换言之,我们之所以要去解悖,是因为我们太过于相信我们自己的常识与理智,而没有想象到某种完满智力的存在。哲学家们耗费了大量心血去“解悖”,但至今也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这是必然的,因为这实际上是想用我们人类的智力去反抗那个“完满的智力”。而在本文作者看来,悖论实质上是文学杰作,换言之,谁只要明白了文学杰作的本质,他也就明白了悖论的本质。 悖论实质上是文学,而且是幽默,换言之,每一个悖论都包含了对某一事物的隐秘否定。 “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悖论:捷足英雄阿喀琉斯让乌龟先爬出一段距离,然后开始追赶乌龟。等阿喀琉斯跑完这段距离,乌龟与此同时也爬出了另外一段距离——尽管这另外一段距离是那么短,却毕竟存在。这是第一个回合。第二个回合在性质上与第一个回合相同,只不过乌龟在阿喀琉斯追赶期间爬过的距离比上一回合更短了一些。由此以往至于无穷,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笨拙的乌龟。 除了结论“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笨拙的乌龟”,悖论中的其它每一句话都不违反我们的经验,都能被我们的理智所理解。悖论合情合理地一路走过来,在它终止的地方突然涌现出一座大山,压得我们的理智喘不过气来。 但这个悖论的结论只是看起来逆情悖理,它却是不可置疑地推论出来的。 文学杰作总会发出某种隐秘的声音。一旦把“阿喀琉斯悖论”视为文学杰作,我们就能听出这样的隐秘声音:谦让总是错误的,因为一旦你作出谦让,则哪怕你只谦让那么一点点儿,哪怕你谦让的对象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但你再想追上他就永远不可能了,所以,无论如何也不可谦让啊。 “谦让”受到了隐秘的否定。 西方有“巨石悖论”:上帝能不能创造出一块连自己也举不起来的大石头?如果不能,这就直接表明了上帝不是万能的;如果能,则表明上帝举不起来他自己创造的那块石头,所以,上帝照样不是万能的。总之,上帝并非万能。 认为上帝“能创造出一块连自己也举不起来的大石头”,这是对于上帝的理想化,被理想化了的上帝也就是所谓万能的上帝。把某个事物加以理想化,总是基于我们对于这个事物的爱,但把上帝进行理想化的直接结果,却是使得上帝触目惊心地表现出自己的无能来。总之,理想化作为一种方法并不是什么好方法,倒是让我们对于事物的爱变成了对于这个事物的伤害。 “厌恶理想化”也是这个悖论的灵魂。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也是一个著名的悖论:蛋都是鸡下的,所以必须先有鸡;但鸡都是从蛋孵化出来的,所以必须先有蛋。 “蛋都是鸡下的”,这是我们能够亲眼看见的事实,而“必须先有鸡”则是我们基于这个事实而得出的常识性结论;“鸡都是从蛋孵化出来的”,这也是我们能够亲眼看见的事实,而“必须先有蛋”也是我们基于这个事实而得出的常识性结论。 常识是什么?常识乃是其内部成员相互对立的、各不相让的垃圾堆啊。 “常识”受到了隐秘的否定。 《五灯会元》卷一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马鸣)问曰:“我欲识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识佛,不识者是。”曰:“佛既不识,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识佛,焉知不是?”[语译:马鸣问:“我想认识佛,佛是什么样子的?”祖回答:“你想认识佛,你不认识的(那个东西)就是。”马鸣问:“既然我不认识佛,我又怎么能知道我不认识的(那个东西)就是佛?”祖回答:“既然你不认识佛,你怎么知道你不认识的(那个东西)就不是佛?”]
马鸣“欲识佛”,就是想要获得某种知识。马鸣现在还不知道佛是什么样子,但佛肯定是马鸣所没有见过的,不过,马鸣没有见过的并不一定就是佛——“佛既不识,焉知是乎”这句话表现了马鸣的怀疑。既然这样,即使我马鸣找到了天底下所有不认识的东西,我也不能断定其中的何者就是佛。 而“祖”的答语“既不识佛,焉知不是”,乃是马鸣单靠理智不能回答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中有这样的言外之音:你马鸣怀疑一切,你固然不会犯错误,但实际上你连犯错误的机会都丧失了,至于你想“识佛”,那就只能是纯粹的梦想了。总之,怀疑让我们连错误的知识都不能获得。 “怀疑”受到了隐秘的否定。 关于“什么是悖论”问题,有着多种不同的说法。本文的理解是:人们根据常识和逻辑而从中感受到了痛苦,但根据常识和逻辑又无法克服这种痛苦的文学杰作,即是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