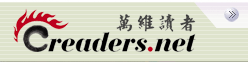�文化沉思录(15) �
庄子感叹:“这些鱼儿游得真是快乐啊!”惠子质疑:“你不是鱼,又怎么知道这些鱼儿是不是快乐?”庄子反驳:“你不是我,又怎么知道我不知道这些鱼儿快乐?”惠子论证:“我固然不是你,但你也不是鱼儿,你不可能知道这些鱼儿是不是快乐,这一点确切无疑。” 这是庄子与惠子之间著名的对话。单从语言外观看,惠子输了,因为庄子只需说一句话,惠子必须用两句话来回应;庄子说两句,惠子就必须说上四句。 如果承认庄子和惠子是这段对话的共同作者,稿费应该怎样在这二人之间分配?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中的名言。一个人不用怎么费力就可以有十个儿子,每一个儿子也有自己的十个儿子,以此类推。一是道的儿子辈(十人),二是道的孙子辈(百人),三是道的曾孙子辈(千人)。到了道的第五代,正好是一万个玄孙——名言里的万物就是这一万个玄孙。这就是人口爆炸。 这段名言似乎是太上老君的人口学。
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我们凭眼睛观察事物而得到的结论,其实都与我们的心情有关系。快和慢,这两个描述物体运动速度的汉字,左边的偏旁,都是心。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不就是客观的认识,而是包含了主观的成分,快和慢等汉字,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清醒和深刻。问题是,中国古人发现了这一事实,却没有因此而不安,也没有想到去解释何以如此,没有像西方哲人那样,为了求得认识的客观性而煞费苦心。 中国文化,不缺乏的是敏锐,缺乏的是永不停歇的求索精神,以及高贵的苦恼。 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与生俱来,这一恐惧也是各种宗教竭力加以制伏的东西。唯有庄子真诚地赞美了死亡。庄子能够看出整个世界是造物主为生命准备的豪华坟场。谁乐意像幽灵一样在这个世界上飘荡,而不想成为此豪华坟场的主人? 孔子之后,儒家相继出现了孟子和荀子两位大师。有人说,更忠实地继承了孔子的是荀子,而不是孟子。但历史事实是:孟子名望之高,非荀子能及。只听说孔孟之道,没听说孔荀之道。 孟子与荀子的历史遭遇似乎表明了这样一点:忠实继承是没意思的。就理论来说,人类天生地喜欢的,是差异,而不是相同(重复)。 常言道儒释道三教互补。其实,儒家内部的孔子与孟子也互补:孔子提供的是从容不迫,孟子提供的是一团火。 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律,就一下子从澡堂里冲了出来,赤身露体,在大街上奔跑,一边没头没脑地喊叫:“我发现了!” 孔子有过类似的发现,结果也是说出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我不想说话了(予欲无言)。”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让学生子贡紧张了起来,马上提醒老师:“您要是不说话,我们这些学生能学到什么?” 阿基米德发现的是浮力定律,孔子发现的是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阿基米德根据浮力定律去解决金属搀假问题,孔子根据天去调整自己的人生态度。 孔子最偏爱的学生似乎是颜渊,其实是子贡,因为,孔子既把自己内心最深刻的痛苦(莫我知)只说给子贡听,又在自己对最高真理(天)有所觉悟后向子贡倾诉。 孔子偏爱子贡,体现了孔子的智慧。子贡没有辜负孔子——其他学生为孔子守孝三年,子贡却守孝六年。 上帝为中华民族准备了孔子,为孔子准备了子贡。孔子临终前对子贡的责备,折射出子贡对于孔子的特殊重要性。 孔子不认为自己是圣人,也不认为自己生而知之,但后世的中国人坚持认为孔子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 老子是通过“致虚极,守静笃”来认识真理,庄子认识真理的方法有坐忘,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大概兼有认识真理的功能。唯独孔子没有认识真理的窍门。孔子似乎一辈子忙于教学、不停地奔走于周游列国的道路上,但孔子说出了最大数量的名言。 不是孔子在寻找真理,是真理紧追孔子不放。所谓生而知之的圣人,是被真理穷追不舍的人。 孔子经历过狂热思想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孔子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 思想不是思想家本人可以自由调节的活动,思想本身是一种瘾,唯一能够解除这种毒瘾的,是新冒出来的思想。一天之内出不来一种新思想,思想家就会抓耳挠腮,就像鸦片瘾发作了。尼采说,一个思想家一天之内发现不了十条真理,他就会在梦中继续追求真理。 孔子饱受这样的痛苦,最终放弃了思想,选择了不费脑筋的学习。 印度人是想象的民族,西方人是理智的民族,中国人是模仿的民族。印度人对历史不关心,西方人从历史寻找真理,中国人要从历史学习为人处事的方法。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从正面受到了苏格拉底的哲学训练,从反面接受了苏格拉底的教训——苏格拉底的妻子是悍妇,柏拉图终身未婚。 孔子的婚姻似乎也是失败的,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不幸短命死矣。如果颜渊不夭折,他大概也会像柏拉图一样终身不婚,不是因为娶不起妻子。孔子把女儿和侄女儿嫁给自己喜爱的学生,最受器重的颜渊却没有成为孔子的女婿,这里面或许有师徒间的一段默契。 《庄子·逍遥游》一开头就描写海里的鲲,“不知其几千里也”。创造出鲲,是为了最终创造出鹏。想象出鲲算不得什么大本领,因为这个鲲是对鲸鱼加以夸张的结果。天空中的鸟儿却实在是没有什么真正巨型的,把鹰夸大一千倍,鹰的翅膀也不足以成为“垂天之云”,再说,这样巨型的鸟又怎么能栖息在陆地上?认为“其翼若垂天之云”这一巨型的鹏是由鲲这一巨型的鱼转化而来,这是庄子想象力的集中表现。 宇宙过于寥廓,生命过于渺小。鲲鹏是庄子反抗宇宙压迫生命的结果。 《论语》记载:孔子不怎么谈论“怪、力、乱、神”。孔子不是对神怪不感兴趣。孔子似乎清楚自己的个人风格,大量谈论神怪会冲击自己的风格,于是,孔子主动放弃了神怪话题。 《庄子》书中,神怪成了真正的主题,庄子也通过谈论神怪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中国文化史上两位互补的哲人,是孔子与庄子。与其抽象地说儒道互补,不如具体地说孔庄互补。孔子在《庄子》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孔子是庄子不能忘怀的人。 《论语》大量记录孔子的话,成了“语录体”的典范。每一条语录都是简短的,但语录体的本质不是简短,也不是命题作文,而是有感而发。孔子说出那些简短的话,不是因为孔子偏爱简短的话。真正的感悟是一闪即逝的火花。 有人质疑我:语录体是孔子那样的圣人才能使用的形式,你怎么也使用?你配吗?我想,此君或许更应该这样质问我:你真的有那么多的感悟? 130亿年前,小得不能再小的宇宙蛋突然爆炸,经过演化,终于有了今天的宇宙——大爆炸宇宙学这样告诉我们。 这样的爆炸让人想起性高潮。公鸡性交过程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似乎谈不上有什么性高潮,所以,即使公鸡有足够的智力,恐怕也不能建立起大爆炸宇宙学。 真理隐藏在宇宙之中,但人类只能发现自己感觉亲切的那一部分。 有人说:《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 《红楼梦》是不是真的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这不要紧。此说法实质上是对《红楼梦》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赞美。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哲学在中国一举成为了“科学的科学”。直到今天,哲学仍然是中国大学学科体系中的第一学科。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只继承、不独创。孔子事实上有大量的独创,却硬要说自己是述而不作,这或许体现了孔子的谦虚,甚至策略,但这一做法在中国文化里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人们以为,连孔子这样的圣人都与独创无缘,你又算老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