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1912~2005): 一代書法大師的愛情, 終成凄美絕唱(蘇炳財提供) (08/09/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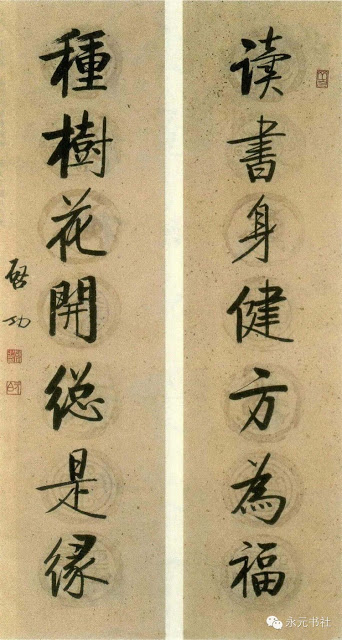

青年時代的啟功
1932年3月5日,是啟功家祭祖的日子。
啟功的祖先是雍正的兒子、乾隆的弟弟。雖後來被列入旁支,榮華富貴幾乎全無,但母親還是十分敬畏這個特殊家世,每年的祭祖簡直就是母親的圖騰。
這一天,母親特意叫了一個章姓姑娘來幫忙,並讓啟功到胡同口去迎接。當時,天上飄著綿綿細雨,啟功來到胡同口,看見對面的林蔭小道上,一個嬌小的女子撐著一把花傘,正裊嬝娜娜地走來。啟功的心頓時像被一隻溫柔的小手摸了一下,情不自禁地想起戴望舒的《雨巷》:這不就是那個“丁香一樣的姑娘”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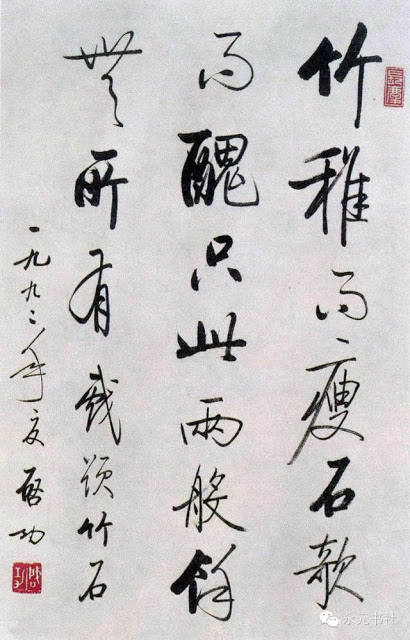
這個“丁香一樣的姑娘”,就是母親和姑姑物色了很久、為他先行相中、而且他也必須要娶她為妻的章寶琛。
當時,20歲的啟功正忙於尋找職業。初見章寶琛,雖恍惚如遇“丁香”,可那隻不過是即情即景的閃爍;待離得近了,卻沒有絲毫心動。然而,母親的態度卻很堅決:“你父親死的早,媽守著你很苦啊!你早結了婚,身邊有個人,我也就放心啦。”孝順的啟功略一思忖,便對母親說:“行啊!人,只要媽看著滿意就行啦。 ”

11歲的啟功,啟功(中)和祖父
裕隆(左)以及姑姐丈在一起 同年10月,啟功和章寶琛舉行了簡樸的婚禮。新婚燕爾,因為章寶琛長他兩歲,啟功便稱她“姐姐”。她湝地笑著,羞澀地低下了頭。婚後,章寶琛操持家務,侍候婆婆,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條。啟功的家很小,朋友卻極多。他們時常來家裡聚會,大家圍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大半夜。每到這時,章寶琛始終站在炕前端茶倒水,整晚不插一言。
啟功的母親和姑姑年邁多病,心情不好時,難免會發脾氣。章寶琛不離左右,日夜侍候,從無怨言。啟功有時在外面碰上不順心的事,回家也沖她發火,她也總是不言不語,弄得啟功想吵架也吵不起來。漸漸的,便有些不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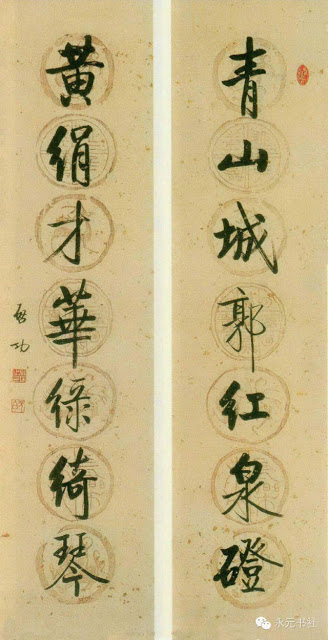
母親說過章寶琛的身世:生母早亡,後媽對她非常刻薄,從小吃了不少苦,而且她是帶著相依為命的弟弟一起嫁過來的。想到這些,啟功內心深處對妻子的同情逐漸化成了愛戀。他發現,這位容貌平常、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難得的知己。
1937年,北京淪陷,啟功丟了國文教員的工作,日子漸趨拮据。一天,他看見妻子在細心地縫補一隻破了幾個洞的襪子,禁不住滿心酸楚。他想賣畫賺錢,但當他背上畫卷準備出門時,又猶豫了。章寶琛明白,丈夫捨不下臉來,便說:“你只管畫吧,我去賣。”那天傍晚,突然下起了大雪,啟功見妻子還沒回來,便去接她。遠遠地,他看見嬌小的妻蜷縮在小馬扎上,身上落滿了雪花。看到他,妻子起身揮舞著雙手,興奮地說:“只剩下兩幅了。”
啟功的眼淚奪眶而出。
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十幾年。直到1952年,啟功出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家境才稍稍好轉。不料,母親和姑姑又先後病倒,兩個重病號就靠章寶琛一人照顧。 1956年,母親彌留之際,拉著章寶琛的手深情地說:“我只有一個兒子,沒有女兒,你就跟我的親閨女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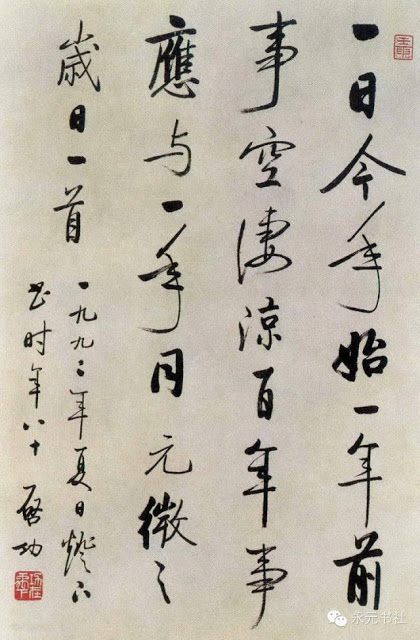
母親去世後,啟功於悲慟中頓悟妻子日夜辛勞的不易,以及對自己的體貼入微。他深感無以回報,便請妻子端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給她磕了一個頭。
1957年,啟功被劃成“右派”。儘管他常以“咱家是封建家庭,我受的是封建教育,劃成右派不算冤”自嘲自解,但終也難掩內心的苦楚。章寶琛心疼啟功,抱住丈夫泣不成聲:“以前那麼苦的日子都挺過來了,還有什麼能夠難倒我們?”她深知啟功愛講話,就勸他:“有些不該講的話,你要往下嚥,使勁兒咽。”聽了妻子這些樸素的話,啟功心頭蕩起一股暖流,終於解開了心頭的死結。
幾年後,啟功重登講台。正當他全力以赴要在學術上進行沖刺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他再次被迫離開講台,一切公開的讀書、寫作也被迫停止。為了讓啟功專心在家練習書法,章寶琛天天坐在門口望風。一見紅衛兵來,她就佯裝咳嗽給啟功報信。為防止抄家,她偷偷將啟功的藏書、字畫、文稿,用紙包了一層又一層,捆放在一個大缸裡,深埋在後院。

1975年,章寶琛積勞成疾,一病不起。她深感自己來日無多,便在醫院裡給啟功交代“後事”。啟功大驚不已,立刻匆匆趕回家。來到後院,拿起鐵鍁,按照妻子說的位置挖下去,果然挖到一口大缸。搬出來一看,共有四個麻袋,一幅幅啟功早年的書畫作品、一本本文稿藏書,竟然全部保存完好!捧著自己的心血之作,啟功的心在顫抖。章寶琛這個不通文墨的弱女子竟敢冒如此大的風險珍藏他的作品,這該需要多大的勇氣!他不由心生感概:一生得寶琛這一知己,足矣!

啟功先生(左一)和夫人(左二)、
母親(右二)及姑姑(右一)在一起
章寶琛一直遺憾自己沒有孩子,而且始終執著地認為是自己的錯。她曾不止一次地嘆息:“如果哪個女子能給你留下一男半女,也就了卻了我的心願。”她病重時,更是千叮嚀萬囑咐:“我死後你一定要再找一個人來照顧你。”啟功說:“老朽如斯,哪會有人再跟我?”章寶琛說:“我們可以打賭,我自信必贏。”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章寶琛傷感地對啟功說:“我們結婚43年了,一直寄人籬下,若能在自己家裡住上一天,該有多好。”啟功的一位好友聽說後,立即決定把房子讓給他們。第二天,啟功便開始打掃房子。傍晚,當他收拾好一切,迫不及待地趕到醫院時,妻子卻已經與他陰陽兩隔。
兩個月後,啟功終於搬進了學校分給他的房子。他來到妻子墳前,告訴她:“寶琛,我們終於有自己的房子了,你跟我回家吧!”那晚,啟功特意炒了幾個妻子生前愛吃的菜,然後一筷子一筷子,不停地夾到她用過的碗裡,直到碗裡堆滿了菜餚。啟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趴在桌上失聲痛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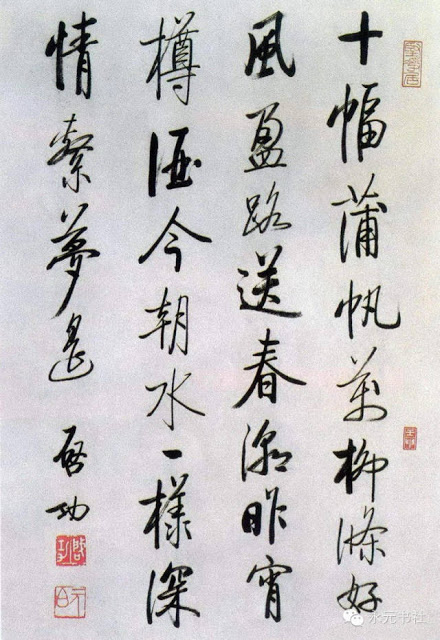
妻子去世後,無兒無女的啟功過著孤獨清貧的生活。對平反後回歸的頭銜和待遇,視若浮雲。他賣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字畫,所得200萬元人民幣,悉數捐給了北京師範大學。自己住在簡陋狹小的房子裡。一日三餐,也是粗茶淡飯。往往一碗炸醬麵、一碟黃瓜就是一頓正餐。他說:“老伴活著的時候,我沒有錢讓她過好日子。現在她走了,我要這麼多錢有什麼用?我們曾經有難同當,現在有福卻不能同享。因此,我的條件越好,心裡就越不好受。 ”
1995年,一位離異女畫家看到他這種生活狀況,紅著眼圈說:“啟功教授,您太辛苦了,你需要一個女人好好照顧。”並要求留下來陪伴他走完後半生。啟功告訴她:“沒有女人能夠取代寶琛在我心中的位置。”女畫家不甘心,幾乎每天都到啟功家裡照顧他的飲食起居,為他謄寫書稿,交流繪畫心得。四個月後,女畫家問:“讓我留下來好嗎?”啟功搖搖頭:“我心裡只有寶琛,再容不下任何女人了。”

章寶琛去世後的20多年裡,啟功一直沉浸在無盡的哀思中無法自拔。他無兒無女,無人可訴,只能將淚與思戀凝成文字,任心與筆尖一起顫抖:“結婚四十年,從來無吵鬧。白頭老夫妻,相愛如年少。相依四十年,半貧半多病。雖然兩個人,只有一條命。我飯美且精,你衣縫又補。我剩錢買書,你甘心吃苦。今日你先死,此事壞亦好。免得我死時,把你急壞了。枯骨八寶山,孤魂小乘巷。你再待兩年,咱們一處葬……”真可謂句句深情,字字催淚。
啟功還有一個最感痛心的遺憾,就是章寶琛在清貧與辛勞中度過一生,從沒有機會出遊一次。所以,晚年時,有人多次邀他遊山玩水,他一律婉拒。因為每當看到別人雙雙相隨,他就會想起過世的老伴,就會心痛。
2005年6月30日,93歲高齡的啟功帶著他對愛妻章寶琛的無盡思戀,溘然長逝。親屬將他的骨灰與章寶琛合葬在一起,了卻了他“來生還要做夫妻”的遺願。
一代書法大師的愛情,終成淒美絕唱。重溫他們從無選之選的包辦婚姻到相濡以沫的一生,讓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人生最可悲的不是難覓知己,而是我們的眼睛只看到自己最愛的那個人,卻看不到那個最愛自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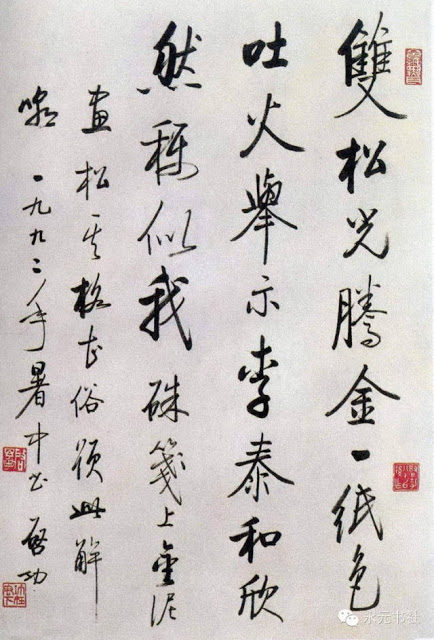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