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28 中国海关杂志 
在我一生中,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钱锺书。
我父亲是搞医的,是研究医学理论出字典的。我最佩服我父亲的一点就是,念古诗,我「嘣」,上句一出来,下句他「咔嚓」就对上!多大岁数啦?他不是搞纯文学的,不是搞古典文学的,真是太地道啦!「文革」之后放老唱片,京剧戏文,上句一来,下句就跟着走。这是什么?这是记忆力!我没有见过这麽好的记忆力。他跟我说,他这一生不知道什么叫头痛。人的一生不知道头痛,等于脑子没有受过任何伤,没有遭受过任何侵蚀啊!其实进「牛棚」、下乡劳动改造,我父亲都经历过。
人临死之前啊,都会回忆。我父亲在弥留之际,哎呀!他中学时候的同学的名字,脱口而出。我差那谁谁80块钱,我什么时候借的,你一定要找到他把钱还给他……什么时候的事?大学一年级时候的事!50年前的事!
其实我是在补充我父亲的遗憾。什么遗憾呢?就是他原来不太同意我干这一行,可能做学问的人对这一行有他的偏见。就觉得你做这行是文化死角。他说的所谓文化死角是学问的死角,也可能我后边努力补充自己的原因就是想补充他的遗憾,使他的遗憾小一点。说不清,道不明,所以我爸给我起名陈道明。我考上天津人艺以后,我父亲最不愉快啦。我是被「上山下乡」逼到文艺界的,是个躲避「上山下乡」的产物。于是乎换来我父亲一声长叹:接受这个现实吧,当个职业做吧。但是你能做别的时候最好不要做这个……但是我始终做不了别的。
再一个是钱锺书。
现在钱锺书一生当中惟一的一本录像带在我手里。他从来不让人拍。因爲他对我和杜宪都不错,在他眼里我和杜宪都属于小孩。你想他送杜宪的是3只小动物的笔。送我的是一条英国人送给他的「三五」烟。还送了我几本他的书,和夫人杨绛的书。并在书上给我写了几句话。那天我说:钱老先生,我想我想我想,跟你聊天的时候拍拍你。他说不会做别的吧?我说我能做什麽别的。他说你拍吧。我去了三趟钱家,第二趟第三趟都录了,变本加厉,有点上鼻子。太珍贵啦!现在3个小时的带子我都转成数码了,全部转到计算机里了,不会丢失了。那会儿「围城」炒得最热的时候我也没往外拿。那是老先生给你的东西,不是给报纸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卖。因爲钱锺书那个年代的文化人没有把文化当商品,你必须尊重那段文化的性质。人家老先生给你小一辈儿的面子,不要把这面子当成不要脸的事儿去做。你不能说拿着大旗当虎皮。钱老先生说我这个角色怎麽出神入化,怎麽超乎他的想象,我不能拿钱老先生的话说事儿。

钱老真是一个大家!但又是南方的一个瘦弱的老人。在他面前你真是不能不低头,肩膀不能不微微往前倾。他往那儿一坐,那种坦然,那种从容。他的意识状态里从不设防。不给自己设防,也不给别人设防。
钱老先生和杨绛先生那种活法,真是一对好夫妻,一对好学究。恬淡,从容,高尚。什么叫大惊小讶?大惊小讶是什么都没见过的。钱老年轻的时候属于吃过见过的。因为吃过见过,所以对什么都已经看透啦,透的不能再透啦。他家里连个录像机都没有,满屋里最响的是一对药锅子,一到点儿就响。他们对知识的拥有已经超出一切啦。一般说这人「学贯中西」。对他们不是这么个概念──「红楼梦」第几页第几行第几首诗的哪个字的解释是不对的……都已经到了这地步啦。咱们评选的「十大文人」有他吗?评一大文人就得是他呀。
唉!在高处立,着平处做,向阔处行,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自律,自洁,自爱,自省──
难啊,好自为之吧!
编者注:谨以此文纪念杨绛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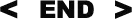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