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岐山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长大,对他的早年经历算是略知一二。
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记得那是1957年,我的父母从上海奉调进京,我和姐姐、妹妹随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岁,我们同住一个机关大院,而他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们两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岁,因此两家的三个同岁孩子,便常常“配对儿”在一起玩。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可惜调到北京不久就领到一顶“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帽子,1958年报中央监察委批准,留党察看二年,行政职务也一并撤销。王岐山的父亲,当年并未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内向,似乎不大喜欢多说话,倒是他母亲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见下文),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亲也是经历坎坷。
王岐山的父亲当年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1929年,他从南开预科考入清华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建筑。那时清华每届也就录取一百多人,王的父亲1933年从清华毕业,在那个年代应该算“稀缺人材”。我后来听王岐山说,他父亲清华毕业去了青岛,工作几年,抗日战争便爆发了,他父亲不愿给日本人干,青岛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没办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亲的老家——山东平度,在山区做教员。
当时的山东,遍地抗日烽火,不过,共产党在山东有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也有抗日游击区,平度,刚好是国民党的游击区。命运使然,平度的国民党看到王岐山父亲很有些抗日情绪,就给这位清华毕业的山区教员封了个“上尉”。及至抗战胜利,青岛成了国民党的五大“特辖市”之一,城市建设迅即提上议事日程,王的父亲当然返回青岛,重操旧业——做城市规划,搞土木建设。
1949年,国民党给王岐山的父亲买了船票,劝其从青岛“撤退”台湾,可王的父亲认为:有能耐,有技术,共产党来了也要搞建设,何必跟着腐朽的国民党瞎跑呢?于是留了下来。没想到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运动后期,党组织一查:王的父亲的那个军衔徒有虚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文革”之后,王岐山曾和父亲聊天,说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说,“也亏了那次抄家,受了惊吓,从此不敢乱说乱动”。王岐山对我说,他父亲的不爱说话,大约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过,“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他父亲却因为“说话少”而躲了过去。直到“文革”爆发,一度领取过国民党上尉俸禄的这桩陈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来。

还好,“文革”来临,知识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亲那时除了挨批斗,就是打扫单位卫生。而我的父亲,却不幸死在了“文革”批斗会上。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记得1980年代初我调回北京,去父亲的原工作单位申请落实政策,要求把“文革”被没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设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搀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谈政策落实事项。看得出来,王岐山和我一样,也是孝子。
我父亲1968年去世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亲——机关大院的居委会主任——崔大妈。我父亲的“问题”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个“文革”期间,崔主任不仅从来没有歧视过我母亲和我们家,还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亲的手坐在床边,好言宽慰。
王岐山母亲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亲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压气氛下,远亲不如近邻,我母亲“文革”后搬离那个大院的时候,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去和热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个招呼,那时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视母亲,也不忘给母亲过生日。
王岐山是1956年从青岛转学到北京的,比我早了一年。我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是上海口音,王岐山则是青岛口音。对于读小学的那些往事,我基本都忘却了,王岐山倒是好记性,他不仅记得我是上海口音,而且回忆说,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班上还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学叫“盖学良”,也有山东口音,因为班上有人笑话他们俩,他们还和那些人打了一架。小时候,我和王岐山关系不错,中学时代我们不在同一所中学,没有很多来往,但“文革”闲得无聊的时候,我们还是常常在一起打篮球。推荐关注:微信查找“华人时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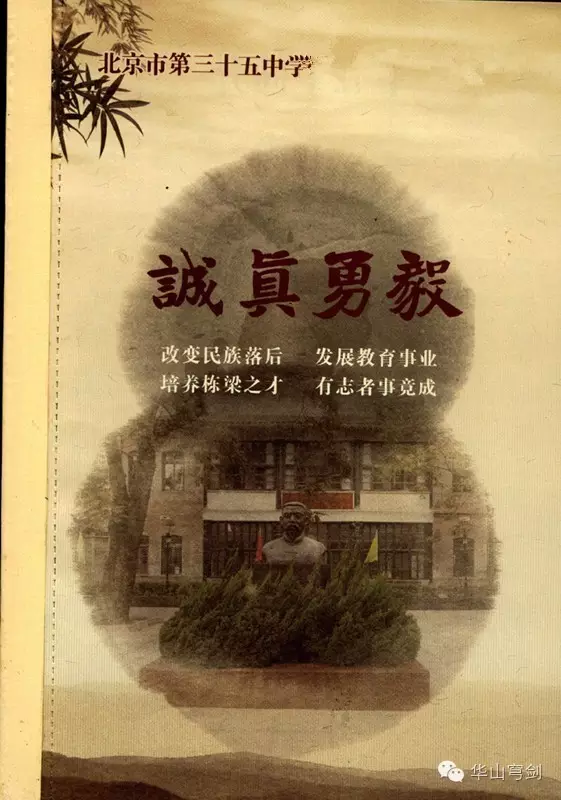
下乡插队之前,我曾隐约听说,王岐山在北京三十五中(北京西城区重点中学)读书期间,曾犯过“小错误”,受过“小批判”,很多年后,我向他求证,他犯的是什么“小错误”,王岐山笑着说:“啊哟,那可不是小错误、小批判,是全校的大批斗呢!”
听他解释,我才知道了原委:“文革”之前,高中年级的优秀学生,常常会奉命担任初中对应班级的“辅导员”,王岐山读高一的时候就担任了初一年级的辅导员。那个班上有个同学颇傲气,一次开会,他坚持说自己的世界观百分之百没问题。作为辅导员的王岐山于是找他谈话,希望他能谦虚点。
王岐山说,“那时候,高中政治课上正好在讲艾思奇的哲学观点,课余时间,我又比较喜欢看书,就把艾思奇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找来看了,我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于是我在和这个同学谈话时,讲到这么一个观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第一,从哲学的高度看,‘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第二,一个人如果这样说自己,未免太过骄傲……”
那个初一的同学当时表示同意王岐山的这番话,但后来,他把王岐山的这些“大实话”——特别是用雷锋作比喻的说法给传了出去,同学们传来传去,传得多了,就走了样,等到“文革”来临,就有人把王岐山的这些话给“捅”了出来,这可不得了了,全校的大会上,同学们批判了“恶毒攻击雷锋”的王岐山。
下乡插队之前,解放军奉命进驻学校,王岐山支持恢复学校秩序,军代表当时就给王岐山平了反。这时候,那些曾经批判过王岐山的同学有点担心,王岐山对他们说,运动来了,谁都可能说错话,办错事……于是相逢一笑完事。
王岐山后来对我说,“很可惜,插队之前,他们把批斗我的照片、录音找来,都给销毁了。要是留到现在,其实倒挺有点纪念意义呢。现在校庆时,我和这些同学再次见面,大家都是很融洽的,谈到往事,都是哈哈大笑”。
下乡插队,我去了内蒙古,他去了陕西,我们没有联系。
(文章来源:凤凰网)
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的同学有一个微信群。2015年3月19日,群里有人发了一则消息:王岐山即将访美,缉拿外逃贪官。有几位同学在消息后点了赞,有人则留言说:“老同学又要发力了。”他们说的“老同学”就是王岐山。群成员刘安琴说:“我们都为有王岐山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他虽然不在群里,但一有关于他的消息,就会有人分享到群里。”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王岐山当年的小伙伴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的风云际会。
1976年7月16日,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学生毕业留念。后排右六为王岐山。(刘安琴 提供)
1969年,不到21岁的王岐山(后排左三)到延安插队。春天刚到,知青们就要学着在地里施肥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
当时的大队支书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知青到来后,康坪大队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
当年在康坪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合影,后排右一为王岐山。
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从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讲解员,23岁的王岐山被录用。和他一批下乡插队,又一起被招到博物馆的吴永琪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对门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就敲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呀?’他说:‘我看会书。’有时候他看书看高兴了还念出声来。”吴永琪说,“我们也看书,但我们拼不过他。王岐山在博物馆工作期间,李先念曾来参观。馆里的军代表一撸袖子说:‘这事我来干。’馆里的革委会主任就说:‘你还是全面负责保安,李先念同志还是由岐山来接待。’”
1973年,25岁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6年7月毕业,上图是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学生毕业留念(后排右六为王岐山)。毕业后他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6年,“四人帮”倒台。各地掀起一场小型政治运动——“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馆长袁仲一(上图)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吴永琪回忆“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学家,被称为‘秦俑之父’,没犯什么错误。他说:‘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灭自己。’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态比我们好,他跟我说:‘你害怕什么呀?!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别人整你,你自己还整自己呀!’我把他这话转告给袁先生,后来大家都挺过来了。”
1983年,王岐山(右)与同事高文斌在湖北赤壁。
1979年,31岁的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民国史研究室的同事发现,王岐山不仅关心学术,还关心国家的前途,很爱琢磨新现象。“那时候广东刚刚有人开始做生意,但我们身边还没有,有一次王岐山问我,你是愿意每月赚90块钱端泥饭碗,还是每月赚60块钱端铁饭碗呢?我想了半天,没有回答上来。我心里琢磨,他考虑的问题都很新啊!”曾与王岐山同在民国史研究室的任泽全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80年代初,王岐山从社科院调入国家农业委员会,1982年,国家农委被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王岐山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
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王岐山还在事业上帮助过很多同事。曾与王岐山一道被合称为“四君子”的黄江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岐山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经常参加有关农业经济和改革问题的研讨,总能提出意见甚至是核心意见,但文章发表之后,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
“岐山乐于在同伴背后做推手,不和别人争功。我遇到过一些干部,下属写了文章,他不仅要署名,还恨不得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他的。两相对比之下,差距太大了。所以,看岐山的学术贡献,不能以文献量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却没他的署名。”
王岐山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历史学、经济学等专业领域,经历了陕西省博物馆、社科院、国家农委等多个部门,“跨界”特点鲜明。但他都能很快进入状态,不管在哪儿都干得风生水起。
日后,他走上从政之路的更大舞台,从防范广东金融风险、抗击北京“非典”、筹办北京奥运会,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挑起中纪委大梁,力推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新气象,也是如此。
他之所以有如此的“穿透力”,把个人的情怀交给国家的命运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坐得住历史研究的冷板凳,也能在经济改革的众声喧哗中探寻方向,还葆有倾听各方意见的虚怀若谷。他的书本里有国家命运。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远行的底气和力量。
诚然,今天的王岐山之所以受人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腐和廉洁政治建设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也牵动着海内外关注的目光。由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青年王岐山为今天的政治生涯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严于律己是一个答案。作为高干家的女婿,他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作为局级干部,他身上的“官气”太过稀薄,以致在干部门诊遭到护士的奚落;作为中央工作人员,他拒绝地方官场陋习,让顶着酒杯跪地的干部灰头土脸……

所有这些,让人看到了一个青年干部顶天立地的正气,感受到了权力的谦抑,更感受到了一个“堪当大任”者对民众发自心底的敬重。这,正是走好从政之路的坚固基石。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十八大以来,气势如虹的正风反腐,不正是基于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逻辑起点吗?不正是为执政党乃至整个社会扫除积弊、涵养正气吗?

从当年嫉恶如仇的“岐山”,到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老王”,他踩着不变的步伐,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